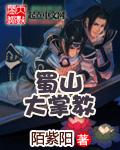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这世界危在旦夕顶点 > 第五十四章 两把大火(第1页)
第五十四章 两把大火(第1页)
1910年10月,中俄边境的满洲里城。
两名被俄国驱逐的中国工人返回境内,在城内客栈投宿。几天后,他们和客栈里另外两位客人在同一日死亡,身上大片的紫黑色斑点。
这一天,是10月25日。
在这之前,两名工人在俄国的铁路工地干活。他们所在的工棚突然有七人死亡,尸体黑紫。于是俄国人将棚里的其他华工一律逐出,烧毁了他们的衣物行李。
满洲里客栈的多人病故引发恐慌,旅客纷纷逃散。就连店主也不得不关门歇业,逃往哈尔滨,但他没能逃过死亡。
店主返回哈尔滨的傅家甸。
这是个房屋低矮、住宅拥挤,聚集了两万多人的贫民窟。此地住户大多是修筑铁路的劳工,从灾害不断的关内来东北谋条生路。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劳工往往数人同居一屋,躺在土坯砌成的炕上,卫生条件极差。这是疫情天然的温床。
店主回家不久也死了,家人悲痛之余为其停尸五日。但很快,其家人也不断倒下,接着是邻居,然后是整个傅家甸的居民。
所有病患都有相同特点,高烧,吐血,死后皮肤黑紫,所以世人称之为“黑死病”。
哈尔滨当时有来自33个国家的16余万侨民,19个国家在这里设有领事馆。西洋人普遍认为要灭鼠,因为这是鼠疫。
可十一月的东北,室外气温动不动就零下二三十度,室内也好不了哪儿去。谁养的老鼠会在这时候跑出来活动?
当疫情在全东北扩散,被中央提前派来的伍连德挺身而出,将接受过简单培训的几千医护和警察派驻各地,一来执行严格隔离封锁,二来宣传防疫策略。
但这事没那么容易。
处在恐慌中的老百姓对官府一向没啥好感。尤其在遍地土匪和日俄势力的荒蛮东北,人们历来是只信自己,不听号令。
民众对隔离充满了恐惧,对检疫人员视若仇敌。当官府要求隔离,他们就将病人藏进衣柜或是草垛,避免被检疫人员带走。
一旦出现病死者,其家人生怕被外界知道而遭到歧视,反而将尸体埋在雪堆下,丢在水沟里,甚至藏在房顶上。
伍连德要求戏院、茶馆、学校通通关闭,商铺必须强行消毒。利益受损的商人便进行抵制,说一粒米、一片肉都不卖给搞防疫的官员。
跟防疫相关的工作都很糟糕。
当在徐世昌和伍连德最焦头烂额之际,国防军赶来了。部队对城市和乡村强行军管,所有人员和物资必须接受政府安排和调配。
暴力机构出手对所有出现疫情的区域进行清查,确保将感染者和密接者从健康人群中筛选出来进行隔离,避免疫情扩大。
国防军第一师的两万五千官兵在十一月上旬抵达沈阳,随即以营为单位向整个东三省的城市和乡村展开。
关键是……有药,还免费治疗。
到十二月初,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的瘟疫传播戛然而止。
东三省的病患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随着部分病患被治愈而返回家中,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有了获胜的希望。
在哈尔滨的傅家甸隔离区,从“南满铁路”赶来的川岛浪速站在几个偌大的尸体堆前。在他身边是上千名哈尔滨的商人、官员、平民,以及各国外交官。
在旅顺的日本关东都督府以“协助防疫”为名,通过“南满铁道会所”向东三省政府捐了15万日元,同时派了一批医护人员到东北各地乱窜。
川岛浪速凭借“防疫”的身份出现在哈尔滨,他冒着巨大风险前来疫情最严重的区域,但抵达后看到的却是善后事宜。
焚尸。
每100具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浇上煤油,然后一把火,上千具尸体燃烧起来。坟场的烟气升空,一时烈焰翻滚,热浪汹涌。
病死者的尸体被冻的硬邦邦,犹如狰狞的黑铁。尸体上还带有大量病菌,土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留下后患,必须焚烧。
川岛很惊讶于东北政府的速度和果决。他深知中国风俗是追求死者入土为安的,这种移风易俗的事非常容易招来激烈反对。
“或许是因为平民被疫情吓怕了吧。”川岛看向围观的人群。当尸体被烧掉,大家仿佛松口气,卸下心理负担。“烧掉也好,至少疫情控制住了。”
被烧的不仅仅是尸体,人们头脑中的某种成见也在这场浩劫中被烧的精光。
因为瘟疫的威胁,东三省的民众不得不跟政府紧密合作。政府也干的挺棒,没让老百姓失望。
东北政府的雷厉风行令普遍百姓刮目相看。它能在旬月间调动两万多军队,组织十几万医护、警察、平民,运输几万吨救济物资并分发。
这分明是一场实战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