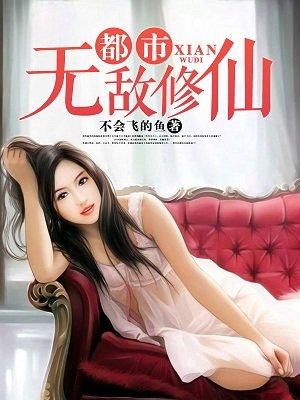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六宫无妃之一路芳菲 > 第946页(第1页)
第946页(第1页)
芳菲做不得声。某一刻,心神恍惚。幸福,其实谁不想安宁幸福呢?弘文帝,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男子‐‐自己于他,也一直是那种复杂的情怀,纵然是亲情也好,爱情也罢,无论什么,都是浓郁的,驱之不散。一个女人,替一个男人生了儿子,要说,两人间,完全是木头一般,那肯定也太假了。顺从了他,这一生,何愁不能幸福美满?至少,没有了煎熬。可是,一些心底的痕迹,如何磨灭得了?‐‐自欺欺人可以,岂能自欺欺天?心里不是不恨的‐‐他见不得自己好。罗迦,无论死生,都见不得自己好。所以,一再的装神弄鬼。就如一个巨大的阴影,横亘在所有人之间;横亘在云山雾海里,举着大刀,阻拦自己所有通向幸福的可能。李奕鼓足了勇气:&ldo;太后,我虽然是汉人,汉人有汉人的礼仪,但是,这是北国。鲜卑人根本不像汉人那么多规矩。丧夫再嫁是非常寻常的事情。先帝已经过世三年了,你何苦如此执着……&rdo;如果李奕这样的汉臣都不介意,其他人,弘文帝当然更有办法去摆平,一切的理论根基,他早已树立好了的。她痛苦地摇摇头,李奕,他不会了解的。谁都不会了解。自己不是要为谁守节,不是为了博得一个贞洁的名声‐‐而是因为痛苦。一种明知有人在暗处,自己在明处,却揪不出来的那种痛苦。&ldo;当日,陛下给我王昭君的画图……你知道王昭君,她照样芳名流传,为世人所敬仰……其实,汉人也罢,鲜卑人也罢,为的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政治诉求,鲜卑人,还活得洒脱一些……太后,其实,你不必那么自苦!&rdo;&ldo;李奕,你该知道,王昭君,她至少当初没有为老单于火殉过。&rdo;正文3369爱6李奕怔住,想起当年高台上的一跳。贞洁热烈的冯太后,如浴火的凤凰,痴迷了北国上下,从此,声名远播,道德和忠贞的楷模,北国历史上,最最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笔从此开始。的确,如何比得王昭君?如今,又是天下归心的太后,抚养着北国人民的希望‐‐拓跋家族的希望后裔,一个善良贤淑,任劳任怨的女性楷模!永远都是楷模。一般人犯了错,不叫错;楷模犯了错,就是大错。坏人偶尔做了一件好事,人们往往会感动,觉得他良心未泯;但是,若是一个好人,偶尔做了一件错事‐‐那么,他很可能成为衣冠禽兽。从太后到皇后‐‐谁敢冒这样巨大的风险?谁敢?人生,就如一个茧子,迟早都是会钻进去,被缚住,然后,终其一生。这有什么办法呢?冥冥之中,天意就是如此。&ldo;李奕,你不用再劝了,我是不会回去的。&rdo;她话未说完,远远地,看见对面,一个白须白发的老道走来。这是通灵道长。每一次见到她,芳菲心里都带着淡淡的怨气,仿佛一如见到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通灵道长已经走近,面露笑容:&ldo;太后,山上寒冷,不如早早回宫。&rdo;&ldo;道长,我该知道,我的任务是在这里照看小太子。&rdo;&ldo;小殿下自然需要看顾,可是,太后,外面的世界也需要看顾。&rdo;道长语重心长,&ldo;太后,现在南朝皇室骨肉相残,民不聊生,无数的百姓想来投靠北国。可是,现有的奴隶政策,总是让他们望而却步,卖儿卖女,都不敢过来。只要稍稍改变现有的土地政策,北国一定会迅速壮大,赋税,兵源都会增加……现在的情况是,朝政被鲜卑贵族把持,汉臣根本近不了皇上身边。他接触的都是那些老贵族,自然会按照他们的谏议办事。太后,只有你出马了……&rdo;正文3370爱7她相信李奕只是出于公心。但是,通灵道长呢?她无法说他出于恶意。也不能说他有恶意。但,总是觉得一切都带上了深深猜忌的符号。总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最悲愤的情怀给予揣测,然后,陷入这样的轮回里,猜猜忌忌,遮遮掩掩,永远是无穷无尽的烦恼。这样敌在暗处,我在明处的日子,真是一种煎熬。这一次,他又是谁的说辞?需要的时候,就让自己回去;不需要的时候,就装神弄鬼?说到底,江山社稷,几分重要?反而因此生了抵触之意,只是淡淡道:&ldo;道长,也许你们高估我了。当今的陛下,他不一定会听我的。&rdo;&ldo;太后,你总要试试。&rdo;&ldo;反正你们不要抱太大希望就是了。&rdo;她甚至直言不讳:&ldo;你们也是知道的,我早就和陛下翻脸了。&rdo;今日一别,便是和弘文帝决裂。二人一时无语。芳菲也无语,甚至不像二人道别,径直地回了慈宁宫。远远地就听得儿子的欢笑声。这孩子,总是笑,很少哭。半岁大的小孩子,眼珠子骨碌碌地追随着地下懒洋洋翻滚的波斯猫。为了怕小猫咪的毛毛钻入他的鼻孔,宫女们总是将猫咪拿得远远的,他每每伸手,总是够不着,如此反复几次,便生了气,非常的郁闷,一而再地,趁势扑过去。小手扑在妈妈的怀里,咯咯地,大声地呐喊,含糊不清的:&ldo;呜呜呜……姆……妈……&rdo;发音不准确,总是这样地乱七八糟,犹如呓语。芳菲听得心潮起伏,纵然是恨天下人,又岂能恨这样可爱的他?抱在怀里,自言自语:&ldo;宏儿……我一定要让我宏儿的路很好走……&rdo;至少,不要像他的父亲,继位之时,左中右突的狼狈和艰辛,一个乙浑,差点将他葬送。正文3371爱8平城,立政殿。小太子的一幅画像,胖墩墩的孩儿,如抱着大鲤鱼的年画娃娃。这画像是弘文帝亲自画的,还是在北武当的日子,对照着儿子,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嘴巴,看他的鼻子……一一对照,事后又加了回忆,工笔细描,小孩子玲珑得几乎要在画纸里跳下来,抱着谁人的脖子撒一下娇。弘文帝每日看完奏折,累了,倦了,总要看看,然后,心底便忍不住的笑意。于是,又觉得加倍的寂寞和孤寒。门外,太监送来宵夜的糕点和参汤。他喝一口,更是疲倦。魏启元如何不晓得他心碎神乱?只一味地开解:&ldo;陛下,您身边真该有娘娘们伺候……如何的,便自苦了?&rdo;他厉了声:&ldo;这话,以后提也休提。朕发了愿,这还不到一年呢。&rdo;魏启元不敢作声,三年斋戒,非同儿戏。可是,如此的下去,身子岂不会熬坏?甚至,连昔日智谋多端的米妃,也不敢再有靠近,更不敢轻易地来进献美人。如此下去,如何是好?平城的冬天来得早,窗外已经是寒风呼啸,弘文帝站起来:&ldo;要不了多久,又要过年了……&rdo;言下之意,魏启元不停地揣摩。难道,又要去北武当了?但是,他不敢多说,更不敢多问。不久,弘文帝收到北武当传来的消息,内容是什么,大家都不得而知,只是,当年的春节,便没有再启程去北武当。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令人意外。第二年一开春,就传来淮北奴隶造反的事情。八十万奴隶揭竿而起,弘文帝一怒之下,连夜召集群臣,商议退敌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