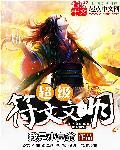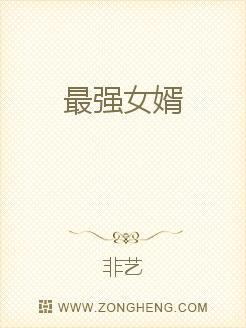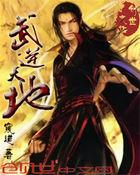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摄政王深得朕心全文阅读 > 第55章 分尸宴(第3页)
第55章 分尸宴(第3页)
姜淼尴尬地笑了笑。
沈玥殷勤地递过来一杯清茶:“仲父喝茶,消消气,慢慢地议。”
……
萧亦然态度强硬,连消带打,一番争议下来,会面不欢而散。
临别时,引路的内监特意带着几人自广盈库侧方绕了一圈,瞧见往来人员清点盘库。
大风掀起盖布的一角,露出二尺高的红珊瑚,坠着各色珠玉。
重利当前,谢嘉澍也算沉得住气,先去了信与各方总舵商议,确信铁甲军南下运粮队只走粮马道,不至于威胁官道封锁。
而后他才私下与沈玥和姜淼密会洽谈,得利分成皆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方才拟约签字。
小皇帝先斩后奏,武扬王被三方排除在外,最终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小皇帝的调令。
萧亦然从北营抽调八千铁甲军快马南下,与先前秦朗带领的两千护粮队汇合,从铁马冰河的手中接手军粮,自行押粮车入中州。
严子瑜想借军粮敲一笔竹杠,令其不得不认他取代严裕良,成为中州严家的无冕之主。
沈玥便借黎家和贪墨案抄家而来的珍宝,占了铁马冰河的车队。
谢家贪心有余、人手不足,不得不默许铁甲军南越逍遥河,替其押粮。
——军粮握在了铁甲军自己的手上,任何想以粮为刀,掣肘漠北的势力,皆被粉碎。
早已接到陆飞白传讯的袁征,与严新雨送家主令入金陵,在保证军粮调出后,便与龙舟分道而行。
袁征与陆飞白挟姜帆和任卓继续南下,九艘龙舟则孤身返航,沿邗沟入海。
改道后的龙舟顺风顺水,现下已经走入了琅琊境内。
【蛟龙入海卷潮回,得偿浅滩之志。】
萧亦然侧卧在榻,看着窗外的纷纷扬扬的落雪,将手中的回信扔进面前的炭盆里。
锦囊三计中的第一计,已悄然奏效。
*
随着黎元明的畏罪自杀,武扬王交出除北营外所有明面上的官职和权柄,沈玥于朝堂的政令得归正轨,亦在有条不紊的推行之中。
先前沈玥态度强硬,朝中上下风声鹤唳,皆以为他会承袭武扬王的作风,继续削官查贪,甚至重开镇抚司的风声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他却并未轻举妄动。
天子剑矛头一转,借着黎家不得已而退让,太后的迁宫,以内府库的贪墨案作小切口,撬动起一场影响后世九州的大民生之举——以开源节流为准的嘉禾新政。
当朝天子虽年岁尚轻,却跟随武扬王历过战火,挨过饥荒,见过最真实切肤之痛的民间疾苦,深知激昂之文易显空泛之理,新政出乎意料的接地气且实用。
沈玥从大内宫制用度削减开始,仅以宫中贵人须着换洗旧衣的小事着手,改制过往后妃帝王衣不必盥洗,冠带帕袜用一次即废的行止,裁剪织女绣娘上千余人——仅此一项便节省宫中开支数十万两。
宫中开了节约的源头,内阁随即效法。
先永贞帝在位四十载,崇道尚乐的奢靡之风,被强力扭转。
嘉禾新政温情与决断并行,沈玥亲至大理寺升堂公审,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将秋狝乱臣的赃银尽数列举,详尽至查抄的每一封官银都清点在册,宣告其贪墨之巨并将名单张贴于市。
大理寺外静坐抗议的闹事者,吃准了历来朝廷于大案要案之上的模棱两可,却在未煽动起更大的骚乱之前,便被朝廷公开的铁证如山死死钉住,成为新政稳固的奠基石。
四大家出乎意料的配合,朝堂上下众人一心。
一场风暴,精准地绕过所有可能爆发的区域,被沈玥牢牢地拿捏在了朝堂之上。
*
此后一连几日,大雪封门,整个中州被笼罩在一片素白之下。
初冬来的格外早些,提前昭示了这必然是个严寒至极的冬天。
萧亦然一早去信递到宫里,提点沈玥除却备粮备荒之外,也应多备炭火木柴,南城民众多贫苦,每逢落雪要加守备巡城人手尽早清扫,以免积雪过重压致房屋倾塌。若城中人手不够,尽管去北营外调。
沈玥日日忙得不可开交,得讯后还是特意微服去了趟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