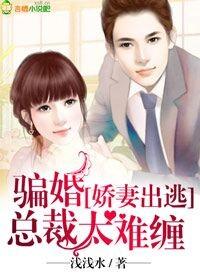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朕真的不务正业 吾谁与归著 > 第一千零三十一章 万般财货弊尽系生民数(第4页)
第一千零三十一章 万般财货弊尽系生民数(第4页)
李如松又领着京营出巡剿匪去了,这次去的是宣府,剿的是草原马匪。
因为天变,北方苦寒,外喀尔喀七部有两部脱离了漠北,迁徙到了漠南,但是漠南的鞑靼人不允许这些放马奴到他们的牧场放牧,冲突开始出现。
李如松率领一个骑营,去了宣府,北上开平府,应昌府,以百骑为单位,开始清缴这些马匪,一直从五月持续到九月。
这次出巡剿匪,是皇帝批准的。
李如松发现个怪事,他在京师镇守的时候,那些文臣就敢对他哈气,喋喋不休,说什么的都有,但每次他出征后,就没人敢胡说八道了。
外喀尔喀部的马匪,完全没有到派出京营的地步,是李如松自己主动请缨。
李如松在京师镇守,任意调动一百人以上的行动,都要层层批准,非常的麻烦。
可是出征在外,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了,李如松手中就真的有兵了,文臣们再胡说,就要担心他带兵回来把刀子架在士大夫的脖子上了。
在京的武官,是斗不过文臣的,强如英国公张辅,战功赫赫,依旧被三杨逼迫到不能上朝的地步。
李如松去草原,更多的是练兵,大明骑兵,破阵有余,衔尾追杀的能力有些弱,更像是重骑兵,而轻骑兵在战场同样重要,缺乏环境,轻骑兵的训练有些困难,正好借着剿匪,把兵练了。
京师十分安稳,凌云翼凶名在外,而且皇帝是驻跸松江府,又不是离开了京城就不回去了。
朱翊钧忙碌了快一个时辰,才把手头的奏疏批完,这还是工作量减半,如果在京师,至少也要两到三个时辰。
他处理完了奏疏,拿起了一本杂报,这本杂报的文章是自由学派的内斗,具体而言,是关于私有财产的确权。
松江本地自由派认为,一切属于我的财产,都是不可侵犯的,即便是国法。
但林辅成则反驳了这个观点。
林辅成是松江府人,他随扈皇帝南下,发现本地学派实在是没有礼貌。
这些松江自由派,有点向极端自由派转化的趋势,林辅成作为自由派的魁首,当然要纠正这些错误。
林辅成在论战的时候,首先确定了私有产权的界定。
自由派魁首林辅成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经过劳动,改变自然的产物,劳动者对其消耗心血、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具有天然的所有权,劳动是私有财产权,唯一正当的源泉。
超过劳动这个限度,任何所得,都应该是公有的,而非私有的。
但当下生产力的限制,导致生产资料归属、生产关系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才会有了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这是当下生产力、生产资料归属、生产关系的局限造成的悲剧,不应该认为这些不公平和不公正,本该如此,是正确的。
私有财产的范围界定,就是林辅成对松江府本地自由派的进攻利器,因为林辅成只用这个界定,就戳穿了松江府本地自由派的根本目的,他们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利己。
故意将私有财产的界定模糊,其实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的必须是我的,不是我的,只是暂时不属于我,终究还是我的。
如此诡辩,为的就是,光明正大的侵占公利,占为私有。
只要把公利侵占到了我的手里,就是我的了,谁都不能抢走。
洪武年间天下均田后,这些田亩怎么就慢慢集中到了乡贤缙绅的手中?大明国初超过数千万亩的官田,怎么到了万历年间,几乎所剩无几了?
这种兼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侵占公利和他人利益,据为己有。
朱翊钧看完了林辅成写的《驳自由私产邪论》一文,不得不说,魁首就是魁首,这格局这气势,几句话把他们的底裤都扒的一干二净,还把他们故意曲解私产界限的目的,讲的明明白白,一清二楚。
他朱批了这篇文章,转发邸报刊发天下。
杂报还有很多,朱翊钧看了几篇,都没有值得在转发邸报的文章了。
他用过午膳后,前往了水师营地操阅军马,和北大营操阅军马不一样的是,朱翊钧在这里会有游泳课,他会游泳,但不经常下水,到了松江府后,他开始每天下水。
大明皇帝,的确易溶于水,但不包括朱翊钧,虽然他达不到浪里白条的水平,但不至于在池子里落水,就直接一命呜呼。
他今天还专门看了看龙江造船厂生产的铁马拖船,搭载最新型的升平十号铁马,拖四到八艘驳船,每艘驳船为一千料,一台这样的拖船最多拖八千石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