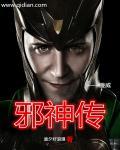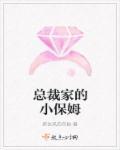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爹唐明皇晋江 > 太白(第1页)
太白(第1页)
文史馆中,李泌好笑地看着李璥。
只见李璥一走进史馆,小小的鼻子翕动了一下,就捂着额头叫了起来,吓得李泌还以为他突发了什么疾病,却见这家伙唉声叹气道:“头疼头疼头疼……看到书我就头疼,居然有这么多书!”
贺监说他“惫懒”不是没有道理的,李璥自称看到书就头疼的毛病,怕是国医圣手都治不好。
“殿下,是我要选书,”李泌提醒道:“殿下是不用读书的。”
“哦对对对,”李璥一下子精神起来:“是你选书,你要什么书来着,我帮你找!”
李泌要选的是以“农政”为类的大型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等李泌挑选出来,就见李璥居然捧着一本书看得很入神,和刚才吵着头疼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
“殿下在看什么呢?”李泌问道。
李璥抬起头,“我方才找到了一本无名氏所著《农书》,这书有21卷之多,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对水旱虫灾作了统计,又提出了救灾措施,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多达200多种。”
“这样好的书,为什么藏在府库之中,”李璥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百姓从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官员切实推行过书里提到的政策?”
“百姓不识字,书写出来自然是要有文化的官员去推行的,”李泌顿了一下,才道:“而官员既然已经脱去了短褐,穿上了罗衣,就不想再去做种粮种菜的老农。”
当年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孔子认为樊迟不可救药,在儒家的观念中,学习是为了做官,而不是去做农民。
李璥摇摇头,“稼穑是国家的根本,本固才能邦宁,如果这个本做不好,大唐所有的煊赫,都是水上浮萍罢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道:“长源先生,我有个想法。”
李泌却仿佛心有灵犀一般:“殿下是不是想推广农书?”
李璥笑了起来,点头道:“我的想法是,修一部大型农业全书,囊括古今农书文献,分门别类,大到经纶康济,小到农桑琐屑,都有据可查。书成之后,颁行郡县,使州郡官吏推行到百姓身上,并以此作为政绩考核之一,不愁官员会懈怠。”
李泌心潮起伏了一下,“此书如果能编成,那一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只是如果要编书,必须要不少的人手,翰林院里的清贵学士,怎么肯干这样繁杂又没有好处的活呢?”
李璥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然哈哈大笑,笑得捂住肚皮,倒像是个扭来扭去的狸猫一样。
见李泌不解,李璥才忍住笑:“这事说容易其实很容易,先生可知,长安城里最不缺的是什么?”
“是什么?”李泌道。
“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李璥道:“这些人有的有秀才的功名,有的只是依靠祖上的名声,但无一例外来长安干谒权贵,想要一飞冲天。”
唐朝的入仕之路五花八门,有的考进士,有的考明经,但都不如一条捷径来得快,那就是干谒。
拿着所写的文章,投递到权贵的门下,如果被权贵看中了,那就可以受到推荐,平步青云,甚至起步就是三品的高官,自然让无数人趋之若鹜。
比如太平公主势大的时候,朝中七个宰相,五个都出自她的门下。
你想见权贵,权贵却不一定想见你。那么多干谒的人,怎么才能脱颖而出呢?那就必须要与众不同,要一举震惊世人才行。
当年有个叫陈子昂的人,没错,就是写“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那个人,来长安求官,谁知两年过去一筹莫展,正此时有个人卖古琴,要价千金。
陈子昂二话不说将琴买下,在众人啧啧声中,说明日我在某地弹琴,想听的就来。第二天数万人来听琴,谁知陈子昂一把将琴摔碎,惊掉众人的眼球,以此成名,冠盖京华。
这就是古代的营销案例。
由此可知,多少人想要得到权贵赏识,不过什么样的人才算权贵呢,自然是能在圣人面前说得上话的。
“好久没去玉真姑母那里玩耍了,”李璥一溜烟便不见了人影:“长源先生,等我的佳音!”
李泌已经知道他要去做什么了,这位汴王殿下,聪明、敏锐,却又沉着、决断……一切要用可能二三十年才能磨练出的品质,似乎上天厚爱,在出生的时候就打包送给了李璥。
他永远神采奕奕,永远精神百倍,再艰难的问题在他的手上都能迎刃而解,他精灵古怪,却又仿佛无所不能。
这很难不让人将他和圣人的其他儿子做对比,李泌这样想着,他不知道圣人是不是也这样想过。
李璥从马上下来,见到玉真观前迎接的女道士,嘻嘻一笑:“灵云,姑母还在请修呢?”
灵云是玉真公主身边的人,见到李璥,微笑道:“公主今日宴客呢。”
“太好了,”李璥高兴道:“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玉真公主是圣人的亲妹妹,出家做了道士,平素在观中请修,但并不是隔离尘世,事实上,公主广为交际,最喜欢品评诗文,谁的诗词做得好,便会对他青眼有加。
看似条件简单,不像别的权贵一样还要考察家世,考察人品,其实最难。玉真公主只瞧得见男人腹中的才华,而这个东西,又是多少男人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