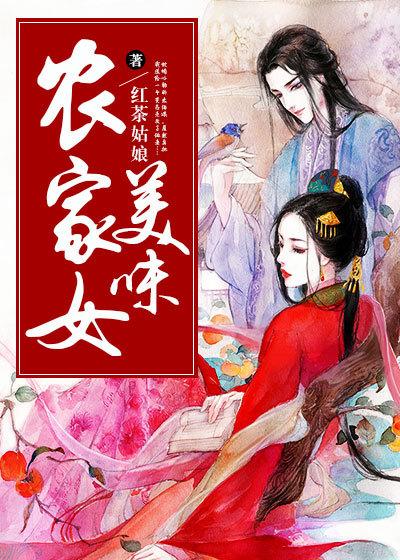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爹唐明皇晋江 > 汴里(第1页)
汴里(第1页)
李璥到底还是没有再要一匹新马,他在宫内的马苑转了一圈,看任何马都不像自己的白乌骓。他依然有骑马的兴致,却再也没有为任何一匹马喂过豆子了。
本来就不怎么进学的他更加惫懒了,除了在江东试点推行曲辕犁之事上颇为关注之外,也就是李泌的清茶能让他兴致盎然。
不过很快他的这一点兴致,也被人剥夺了。
李泌要去开封处理百姓抗税一事,这事情也拖得蛮久了,久到圣人发了重话,如果太子不能顺利解决此事,朝廷就会派遣官吏接手。
朝廷派遣官吏,那也就是移交到李林甫的手里。
李泌是太子手中的王牌,在这件事上他必须要承认李泌说的是对的,他的税法可能从根源上出了点问题,那么既然李泌有先见之明,这件事交给他去解决,似乎也理所应当了。总之太子不可能派遣其他的心腹如韦坚或者皇甫惟明去,这两人都位高权重的,不适合处理此事。
这就很让李泌不高兴了,因为李泌走得匆忙,居然没有向他告别。
“我们先生说,等他回来,一定亲自向殿下赔罪,”服侍李泌的小道童一本正经地转达李泌的话:“到时候任由殿下发落。”
“我哪敢发落太子哥哥的人啊?”李璥拖长了声音道:“……还是太子哥哥说话管用啊,一句话就可以任意差遣,我还真以为太子待他是以宾客之礼呢。”
小道童稚嫩的脸上露出一丝懵然。
李璥倒不是要为难他,只是为李泌稍稍不平罢了。这种奔走的事情,他以为太子手下能人辈出,总不至于叫李泌亲自奔走一趟,结果出乎意料,李泌不仅要出谋划策,恐怕还要身体力行。
“好了,”李璥眼珠子一转,却忽然嘻嘻一笑:“我可不想等候他的佳音,倒不如我亲自去寻,给他一个惊喜。”
李璥去开封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封国就在开封,王府也建在开封,是北魏时期一个名臣府邸改建的,他还一次都没有住过。
“儿子先去藩国巡视一下,然后在洛阳迎候阿爹和娘子,”李璥不仅把自己安排地明明白白,顺带也安排了圣人和娘子:“阿爹十一月起程东巡洛阳,如果还要北巡并州的话,那得再延迟一月……不过过年之前,儿子肯定能见到阿爹。”
“你去藩国干什么?”圣人道。
“不是说,开封抗税的事情,闹得很厉害吗?”李璥一摊手:“那可是儿子的财源之地,百姓不上税,儿子的钱袋子就瘪了,儿子总得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吧。”
“你个小财迷,”太真点了点他的额头,无奈道:“原来是想着钱呐。”
“无钱说话如放屁,有钱说话屁也香。儿子看着风光,其实欠了一屁股债。”谁知李璥掰着指头数道:“欠了宁王孙的一只大公鸡,居然要我二千两银子,黑心啊黑心……欠了张婉儿波斯螺子黛十盒、蔷薇露十瓶,她也真敢开口,娘子这里的蔷薇露才三瓶……”
“你还欠了贺监不知多少堂课业,还欠了朕八十板子!”圣人哼了一声。
“板子就免了吧,儿子这小身板不经打啊,”李璥道:“打坏了我,到最后心疼的是娘子,岂不是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圣人被气笑了。
“意思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李璥道:“阿爹肯定是舍不得让娘子蹙眉的。”
太真“扑哧”一笑,眉目间倒是难得有一丝羞赧,不过更多的还是雨露滋润后的娇艳欲滴。
“滚滚滚,”就听圣人笑骂道:“想去哪去哪吧,别在朕面前碍眼。”
李璥得了允准一跃而起,抱住太真的脸庞狠狠亲了一口,亲的太真咯咯直笑。
在便宜老爹成功黑脸之前,李璥已经撩起袍角,一溜烟跑出了兴庆殿。
李璥说出发就出发,一路快马加鞭昼夜行至河南。
他本以为自己追的上李泌,结果直到周家口镇了,也没有碰到人,看来李泌也走了夜路。
周口镇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交汇处,李璥抵达的时候,就看到四面黄水如注。
来的时候李璥就听说,今年黄河发大水,不仅冲垮了故道,还从贾鲁河入了海,如今贾鲁河虽然还是一片汪洋,但水势已经减了许多,露出河两岸黑黝黝的土地。
李璥看了半晌,不见一个百姓,不由得道:“奇怪……”
“怎么了,殿下,”王兴贵道:“……公子?”
李璥编修农书,他知道河水冲刷过后,会留下一种厚厚的黑色淤土,这种土能肥田,庄稼要是种在这种土里会长得好。
所以每次黄河大水之后,总会有百姓挖这种淤土,但眼前找不到一个……还是有一个的。
一个老汉坐在土堆上,双目无神,不知道看着什么。
“老人家,”李璥走了过去,刻意隐去了关中话,用河南的官话道:“今年河水淹了地,家里有没有存粮啊?”
这老汉看了他一眼,见李璥是个唇红齿白的小金童,有些喜爱;但再见李璥周身无一不是金织玉绣,目光不由得瑟缩起来,含混道:“啊,有、有的。”
“听说今年朝廷蠲免了赋税,”李璥心中一动,又问道:“老人家,日子还能维持吧?”
这老汉又“唔唔”了两声,就在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爹,快回去吧,里长又来催租子了!”
一个农妇站在陇头上喊着,这老汉像触电一样站了起来,颤颤巍巍扔下拐杖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