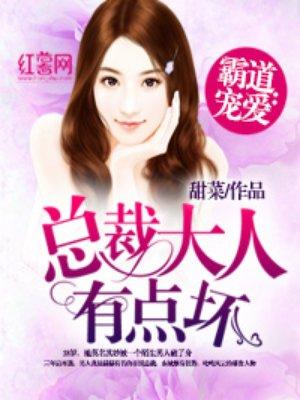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缇萦的读音是什么 > 第18章(第2页)
第18章(第2页)
&ldo;叫我就不!&rdo;缇萦大声地说,像是跟什么人抗议。
&ldo;那你就等着吧!&rdo;卫媪随随便便地答了这么一句。
&ldo;等?等谁&rdo;?缇萦猛地里醒悟,原来卫媪说了这半天,是取瑟而歌,认定她的矢志不嫁,只是为了朱文‐‐
于是,缇萦简直怒不可遏。她认为卫媪不仅冤屈了她的本心,而且亵渎了她的孝心。然而她也知道,争吵辩白,都不能改变卫媪的偏见。只有一个动作可以明志。
本性中得自母体遗传的九分柔顺,此时敌不过得自父亲遗传的一分刚烈,缇萦悄悄站起身来,摸着一柄小刀,学她父亲的样,把朱文所赠的那件紫色绣襦悄悄地割成碎块。
发觉缇萦的动作有异,卫媪问道:&ldo;你在干什么?&rdo;
缇萦不答,摸着一块旧布,把割碎了的绣襦包了起来,准备弃掉。
卫媪越发生疑,细想一想刚才所听到的&ldo;嘶、嘶&rdo;的声音,始终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何事?于是,她摸索着出了西厢,取来一只雁足灯,往席上一照,赫然一块块割碎了的紫罗,依稀还可辨识出绣的白花。
&ldo;这是什么?&rdo;卫媪诧异地问着,一眼瞥见那个没有能包得严密,有紫罗碎片垂在外面的包裹,和缇萦面前的小刀。这就不须她回答,便可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于是,卫媪震惊了!震惊于十四年来第一次发现,缇萦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是愤怒,也还有恐惧、惋惜和失悔。这一切加起来的滋味,很不好受。
&ldo;哼!&rdo;她冷笑一声,&ldo;你,你真是你爹爹的好女儿!&rdo;
缇萦心里也难过,想哭;但奇怪地,隐隐有种莫可名状的力量,止住了她的眼泪,只冷冷地答说:&ldo;这下,总干净了吧?&rdo;
见她是如此倔强偏执的态度,卫媪越发生气,同时也深深警惕,缇萦不再是会撒娇、会哄人的小孩子。人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说话行事会不给人留余地,总之,有距离、有隔膜了。
这使得卫媪很伤心,一语不说,悄悄地转身而去。
独对孤案,缇萦觉得好生无趣。心里空落落地,天地之大,仿佛没有一样事物值得一顾。就这样怔怔地坐着,让一些毫不相干的念头在方寸之间流过,身如岩石、心如槁木。
忽然有个叫她动心的声音出现了:&ldo;缇萦,缇萦!&rdo;
定神看时,是父亲在她房门口。
&ldo;爹!&rdo;她赶紧答应一声,飞快地站起身来,看见那块碎罗,顺手一捡,抛在屋角,然后迎了上去。
&ldo;去取些酒来我喝!&rdo;
&ldo;是。&rdo;缇萦口中高高兴兴地答应着,心里却不免忧疑。淳于意的日常生活,甚有规律,除非遇到极不痛快的事,夜间是从不喝酒的。
因此,她到厨下取了酒,切了盘风干的鹿肉,又盛了盘干果,一起送到东厢。借侍着钦的题目,就不肯走了,她要看看父亲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快?
这一时不容易看出来。淳于意和宋邑都默默地饮着酒,脸上也都是有心事的神气。这僵硬的空气,使得缇萦难以忍受,于是她挑起了一个话题。
&ldo;宋哥哥,唐哥哥近况如何?&rdo;
那是问唐安,&ldo;他还好。仍在齐王府当侍医。不过‐‐&rdo;宋邑突然改口问道:&ldo;五妹妹,你到临淄去过没有?&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