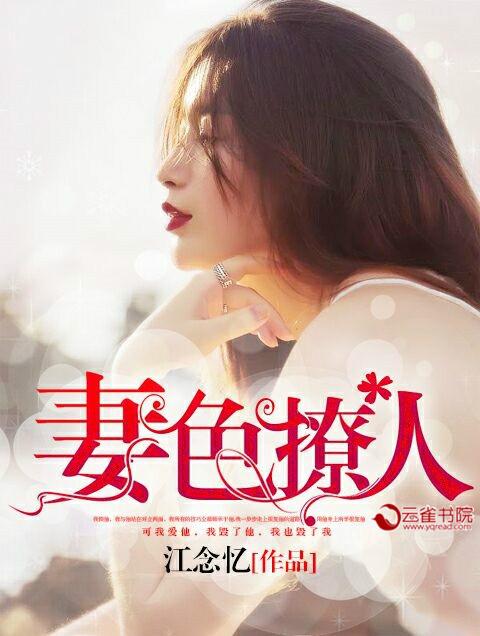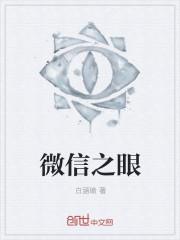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燕食记月饼 > 第十二章 戴氏本帮(第3页)
第十二章 戴氏本帮(第3页)
明义点点头,对凤行说,好,爸明天休息,就给你们做。
第二天黄昏,明义去了街市,挑了上好的五花肉。说是好,连上皮肥瘦夹花,得有七层。想想孩子们,顾不上手里紧巴,整割了三斤。路过上海老乡开的“同福南”,又买了百叶结、水笋和老抽。
大火烧,小火炖,中火稠。到孩子们快放学,这锅肉刚刚收汤,算是好了。明义也很满意。浓油赤酱,焦亮糖色,在这本帮菜的红烧肉上,才是无可挑剔。那扑鼻的香气,在公共厨房里飘了出来。
一个隔壁福建街坊的小孩,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身后,眼巴巴地看他。他懂了,洗净了手边一只小碗,盛了块肉。放在这孩子手里。这孩子似没见过这肉的做法,打量一下,小心翼翼地咬一口。眼睛渐渐亮了,是欣喜的内容。他飞快地跑出去,再回来时,身后竟是拥拥簇簇的一群孩子。每人手里,都捧了一只碗。明义看看他们,又看看锅里的肉。没怎么犹豫,给每一个孩子都盛了一块。孩子们吃了,兴奋地用福建话议论着。领头的那个孩子,对他鞠了一躬。明义将锅里剩下的红烧肉盛出来,淡淡苦笑。大海碗,竟只有小半碗了。
晚上,自家孩子,都只分得了一块。小弟阿得“啊呜”一口就吃完了。吃完看看碗里空了,号啕大哭起来。老五说,爸,这北角以往都是上海的有钱佬。咱们可不是。
明义沉默。七姐凤行,将自己碗里的红烧肉,悄悄拨到阿得碗里,自己扒白饭。
第二日清早,素娥看到门上挂着许多福建的吃食。千丝万缕缠绕着红线的,是闽南的平安粽。
很快,便有街坊的大人,来跟明义讨教这红烧肉的做法。明义耐心地教他们。见他们不得要领,干脆跟他们下到厨里,手把手地教。做好了,彼此都欢喜。街坊们千恩万谢着。明义笑笑说,莫在意,小囡吃得适意就好了。到了吃饭的时候,街坊就敲开了门,递送来自家做的下饭菜。
再后来,街坊家里要请客吃饭,老人家要做寿,小孩过百日,都将明义请过去,帮他们做一个红烧肉,便也留下他喝酒。明义的这道菜,竟在四邻做出了名堂。本帮的红烧肉,原有十六字的秘诀,叫“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赴了几次街坊的筵席,明义便也总结出来,福建人的口味亦有浓厚处。这与烹调原料多取自山珍与海货有关。也喜用糖,善用糖甜去腥膻。并且讲究“甜而不腻,酸而不峻”。这么说来,竟与本帮菜的做法是不謀而合,也就不奇怪他们何以如此喜欢他做的红烧肉了。
有次,他所在国药公司的叶老板,孩子考上美国的大学。也请他去饮宴,又请他做了拿手的红烧肉。席上惊艳一片。老板与他饮酒说,我们福建人吃的,那是“一块润饼打天下”。阿义,你是真人不露相。老板太太就说,没承想,你们店里藏龙卧虎。阿义这手好厨艺,不开个餐馆可惜了。
明义嘴上客气着,只当这是玩笑话。回去说给素娥听。素娥也笑,说,真要是开个馆子,依我老公的斤两,只怕门口要排长龙。
夫妻两个,就都哈哈地笑。素娥看明义,笑得眼角都是褶子。她有些心疼,看出这笑里,有知足、有认命,也有老。
到了第二年,一日清晨,明义照常去店里上班。老板叫他将前一天营业所得款项和支票,拿去银行存款。刚刚回来,就看到店外嘈杂。一些警察在门口,正跟老板和几个伙计不知在争论什么。警察声称店里的货车违例停泊,入内抄牌。即时将店里的人都扣押了。明义看老板从后门
出来,手上戴着铐。就挺身上去,警察喝问。老板的声音更大,说,让他走。他是个外乡人,连福建话都说不利索,不关他的事。
明义回到家,失魂落魄。老板被捉走,没再回来,几个伙计也是。被定了非法集会的罪,判了两年。在北角待久了,阿义自然听说这一区是香港的左派基地。“六七”余温未去,气氛还很紧张。听街坊说,他任职的成药公司加入左派设立的斗争委员会,老板是爱国商人,又是福建同乡会副会长,一直受港英政府密切监察。近日因接近节庆,装修店面,早就被警方盯上了。
明义想着,老板话不多,但人细心厚道。过年时,给他家众多子女,一人封了一个利是。
店被查封了,他的工作没了。他只靠窗坐着,望着外头的灯火失神。素娥说,没事,再难,还能难过吃不饱饭的时候?
他笑笑,依旧向外头看着。春秧街上的电车,叮叮当当地响,声音有些倦,像夜归的孩子。
过几天,家里来了人,是老板的太太。明义刚想安慰她。却看叶太太手里执着一个包,交于他手里。叶太太说,阿义,我们同乡会的人,集了笔钱。不多,但够你开个店做生意。渣华道阿水伯的糖水店,年纪大了开不下去。盘过来,开个小馆子吧。你一手好手艺,莫浪费了。
明义不肯接,连连推让。
叶太太把住他的手,实实在在地。她口中说,这年月,谁都不易。这一区的上海人,走得七七八八了。你不靠我们,能靠谁?
明义立时,就哭了。一个大男人,哭得没成色。他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哭。
两口子就商量,开了餐馆做什么。
素娥就说,街坊们爱吃红烧肉,就做红烧肉吧。
明义说,红烧肉不当饱啊。
凤行在旁边听见了,说,那就开个面馆吧。红烧肉和辣酱当浇头。
做爸妈的听了,都心里称好。想这小囡真是灵。
他们就给面馆起了个名字,叫“虹口”,是明义以往做救火员的地方。
店面装修好了。素娥找出明义穿着制服、在救火会大楼前拍的照片,去了英皇道上的照相馆,翻拍了一张大的。明义写给素娥的第一封信,就夹着这张照片。照片上的明义是个意气风发的样子。他一手叉着腰,一手遥遥指着,方向是身后六角形的塔楼。素娥把照片镶了框,擦了又擦,稳稳挂在墙上。
开业那天,街坊们都来了。送了个花牌,也是热热闹闹的。上面写着“门庭若市,日进斗金”。
虽不至日进斗金,但生意确实很好。明义和素娥,都没把它单当生意来做,倒像是每天热火朝天地给家里人做饭,心气儿十分足。一大清早就起来备料,熬高汤。肉自然要当天新鲜的。为了便宜些,明义蹬一辆三轮车,自己去肉食公司买五花肉,也还是一块块地挑。久了,人家都知道上海师傅是个精细人,糊弄不得。至于面呢,则是对面“振南制面厂”送来的上海碱水面,高筋面粉制成,又爽滑又筋道。出锅后,明义照例要在凉开水里,先醒一醒,咬劲儿就更足了。
午市开了,来帮衬的先是附近做生意的街坊,鱼档果栏的。再是附近电车厂交班的司机大佬、丰华国货的售货员。到了晚上,那可就热闹了。因为街坊孩子们都放学了。家里大人忙的,干脆给他们在明义店里包了伙。长身体的时候,格外地能吃,一大碗哗哗就落了肚。明义看他们吃得满头大汗,就拎起勺,给他们添块肉、加勺汤。子女们回家早的,也都懂事来帮忙。可是铺子小,后厨又热。明义和素娥,就将他们赶回去。唯有凤行,赶不走。两个老的,见这孩子不吱不声,见缝插针把该干的事,都给干了。间隙还不忘了温习功课。到了夜里,过了一点,最后一波下晚班的工人吃了消夜,走了。店里才算是能喘一口气。两个老的,互相给对方揉揉肩膀,捶捶腰。看着灯底下,是凤行瘦弱的背影。这小囡还坐在小板凳上,埋着头洗碗,仍是一声不吭地。两个人心里就又心酸,又安慰。
“虹口”面馆,就在北角扎下了根,一做就是许多年。明义和素娥,渐渐地老了,儿女们也长大了。
面馆就着那个小门脸儿,生意没有做大,其实名气是大了。外区的客人,经常慕名而来,就为了尝尝戴老板一口“入口即化”的红烧肉。有些师奶,竟然要明义面授机宜,教那红烧肉的做法。按理说,这于店家很不合规矩。但明义笑笑,一五一十地教给她们。然而,她们回去照样做了,还是烧不出明义店里的味道。就越发敬佩戴老板,口耳相传,帮衬得越发勤了。
这些客里,总有一个马姐,夜色将近的时候,拎着一只提篮出现在店门口。那提篮是老物,很精致,把手上雕着花。篮身上,也还辨得出,是凤穿牡丹的图案,虽然已经褪了色。提篮里头,还
装着一只骆驼牌的保温桶。这马姐总是站在外面等着,也不进店堂。打上一碗面,就走了。人安静,和明义也未怎么交谈。印象里只第一次,面打好了,看一眼,说,唔好意思,我家主人唔食芫荽。她的广东话,有外乡口音,声音软糯。明义记住了,自此便再没有放过香菜。
这马姐陆陆续续,来了有几年。有一阵子,香港台风挂了“八号风球”。她不来了。明义和素娥两个,竟有些记挂。其实萍水相逢,记挂的是什么,兩个人也不知道。但就是隐隐有些担心。一个月后,她又来了。明义回头看看素娥,素娥眉眼里也是如释重负的笑意。
明义就下厨,烧了一个烤麸。另装了一碗,一并给马姐放进提篮里,说,这碗是送给你家主人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