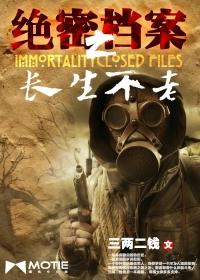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彼岸父子by凌未陌 > 8 第8章 情起不知何所言四(第1页)
8 第8章 情起不知何所言四(第1页)
翌日天未亮,陌北的门便被叩响了,开门发现南笙立在门外,见他便道:“师兄,可以去了吗?”
睡眼朦胧的陌北却一下子倒在了南笙的肩膀处,缓慢而均匀的呼吸声传进她的耳朵,温热的水汽拂过她的脖颈,她一时不知所措,只得呆呆立在那里。
时间流逝而去,垂柳叶上的露珠滴滴落在地上,清晨的陆青观静谧得连露珠滴在地面上的声音都清晰可闻。耳边是陌北均匀的呼吸声,四周没有一人,她也不敢大声叫他,只能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却发现太重了,根本不能推开他来。
阳光寸寸溜进陆青观,被四周的景物切割成无数不成形的影子映在窗棂门框赤柱之上。南笙无奈立在那里,直至整个陆青观沉浸在潋滟的日光中时,陌北才悠悠然醒来,看着眼前的南笙,一头雾水地问道:“你怎么……?我怎么……?”
南笙不知如何作答,只得撇嘴,耸耸肩问道:“师父会不会罚我?”
陌北脸色瞬间黯淡下去,一副大难临头的模样,哀声叹道:“不止你,我也逃不了。”他摇着头,“唉,贪睡一时,受罪一世,你怎么就不知道叫醒我呢?”他倒埋怨起她来了,这让南笙愈加不知如何应对了,只能摇头苦笑。
冠宇是个极度严苛的人,那日二人没能完成晨练的任务,理应受罚,只是陌北没想到,竟会罚得那么重。冠宇命二人均到后山去思过壁前思过三日,同时还得顶着个一尺大小的玉碗,碗中盛满清水,且三日不能进食。只是,渴了的话,可以饮那碗中之水。
南笙心中纵有万般埋怨,却也在陌北那张洋溢着歉疚的微笑脸下消弭无形了。陌北倒显得尤其失落,南笙见他百般不情愿地将玉碗顶在头顶上,不禁问道:“师兄往日可受过罚?”
陌北嗤笑一声,说道:“自上山以来,谨遵师父教诲,每件事儿都做得中规中矩,自然从没受过任何处罚,却不想,你一来,就陪你受了这等罚,你说,我冤不冤?”
南笙险些笑出声来,反驳他道:“怪起我来,师兄难道不知道那日是你自己没能起得来吗?说这话,羞愧否?”
被自己这小师弟一揶揄,陌北自知辩不过,那日的确是自己没能起来,所以怎么都是失了理,便不再狡辩,忙不迭道歉道:“见谅见谅,许久未曾晨练了,一时不能适应自然是常理之中的事儿,只是连累师弟你了,算是我对不住你,日后定然不会了。”南笙听他这么说,心中便也早没了怨气,只说道:“罢了。”
三日处罚之后,南笙与陌北便不敢再出什么岔子,此后的每日都能按时起来,只是开头那几天,南笙因着身子弱,加上南禺山地势险峻,并不好走,以至于那几日都未能在日出之前回到观中。师父只责备了几句,也就算了。随着日子过去,南笙倒是能明显觉出自己日渐强健了起来。
晨练大抵用了两月时间,冠宇见南笙体格差不多了,便不再要她做晨练了。他叫陌北开始着手教她剑法基础,这一晃,又是数月之久。气候渐渐变化,初冬时分,南禺山便开始飘雪,不下几日,整个陆青观便被皑皑白雪覆盖,观中银装素裹,好不壮观。
南禺山遍布红叶枫树,深秋季节里烧的火红的枫叶在缱绻的寒风中渐渐没了影踪,只有在雪化了的时候,能在白雪的间隙中瞧见几片坚韧的落叶埋在雪地里面,稍稍点缀了这一地的荒芜与静寂。
还未入冬的时候,南浔派人给南笙送了些过冬的衣物,还有许多滋补身子的药材。当然,冠宇与陌北也少不了得了些好东西,于是二人顿时对南笙刮目相看起来,都在心里揣摩着她是哪家的公子哥,家底一定甚为厚实,不然哪能有这么好的福气。
陌北平日里看南笙总是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觉着她必然出自书香门第,而令他更为佩服的却是南笙那一副绝妙的书法。他也练过书法,功力不浅,曾一度被家人称赞不已,但却在看罢南笙的书法之后,佩服得心甘情愿。
也许是在这山中太久,平日里总是练武习剑,久之便生疏了书法。陌北觉得,自己是时候该回去了,他来这山上,唯一的目的便是想要让自己体魄强健起来,两年过去,他身子骨早已不似当年那个病弱的模样,不仅如此,还习得了一身好武艺,他日回去,定能干一番大事业。
他犹记得那年在市井中无意听到的南禺山,便觉得那是自己的一个机遇,于是便辞了自己娘亲,来到了南禺山。那时师父并不理会他,他在山门外足足跪了七日,最后没了知觉,醒来的时候,师父才勉强收下了他。
现今,离那个时候,竟已经有两年半的光景儿了。陌北想走了,可他发现,走不了。他站在剑柳宇门前,立在台阶上面,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忍不住叹气。南笙见他这般黯然神伤的模样,关切问道:“师兄可是想家了?”这话,竟一语道破他心中所想,他无奈回她道:“想,是真想。”他伸手接住几片雪花,语气落寞说道:“在我的家乡,每当下雪之日,便会兄弟几人去打雪仗,可我那时身体不好,便没有那个机会,只能羡慕地看着他们玩耍。可现在,身体好了,却也是再不能做哪些孩童的乐事,人生在世,能有几时,是快意地活着呢。”
他这一席话,真真说到南笙心里去了。她第一次听陌北提起自己的事儿,却觉得他们的命运是那么相似。来之前略有耳闻陌北的事情,不过是那个给自己看病的神医说的,几分真假着实难辨,但现在听了陌北的话,总算是能分得出些许真假来了。
小时候的她,却也是什么都玩不得的。但现在的她,许是可以了吧。想着,便几个步子下了台阶,置身在皑皑白雪之中,蹲下去抓了一把雪,触不及防地朝着陌北扔了去。雪团一下子打在了陌北脸上,他顿时哭笑不得。而南笙看着他只是笑道:“今朝有雪,何不享乐玩焉?别白白浪费了老天爷给你的机会。”
听得这话,陌北没有弹掉身上的雪,一个飞身立在了雪地之上,拾了一捧雪,朝着南笙砸了去。
此间的陆青观,独独只能听闻二人的嬉笑声。冠宇撑开窗门,看着南笙和陌北嬉玩的身影,嘴角莫名升起一抹笑意,兀自抱着暖壶立在窗户边上,静静看着他们。
南禺山的冬日在无止尽的白雪中悄然逝去,时光如同被寒气冷冻的湖面,看似停住,却无形中,冰面底下的那些水,早已悄然溜走了。于是神彧纪一百四十六年款步而来,带着残存在春风里的寒气,一点一点渗透时光的细枝末节,然后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春意盎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