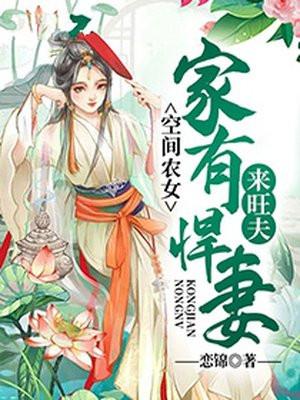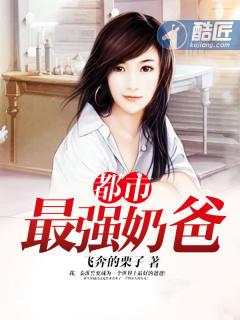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济公传奇52集在线观看 > 第701章 请师母做冰人(第1页)
第701章 请师母做冰人(第1页)
光阴似箭如水流,梁祝二人在尼山书院里攻读,已经有两年八九个月了。
一日,梁山伯在练习字体书法,祝英台伏在桌案边,用毛笔调和墨丸。这墨丸是用以炭黑、松烟煤和胶这些东西做成的。那时,已经不用竹筒盛汁,改用凹心砚。
祝英台研墨的砚台是黄铜制成的,是一个龙头乌龟驮着凹的小山台的形状,很是别致。
英台将墨丸调和以后,用笔染了墨汁写字。祝英台尽管伸着头,用毛笔的毫毛轻轻地按压调和墨汁,身子上半截则横在桌案当中。
梁山伯看见祝英台半边的脸上溅了几点墨汁,于是掏出手绢,给祝英台擦掉。
梁山伯拿着罗绢,正在祝英台脸上擦,看见祝英台的耳朵的耳垂上有耳环的耳洞,于是好奇地问道:“英台不是女儿身,为何耳上有环痕?”
祝英台闻言,巧言掩饰,说道:“这耳环痕是有原因的,梁兄何必起疑心,只因为村里酬神还恩,多有庙会,每年的观音成道日,村子里每年都会举办朝拜观音会,年年由小弟装扮观音,梁兄呀,你做文章就要专心,你前程不想,想钗裙。”
梁山伯听了祝英台这样想,笑了笑,说道:“从此我不敢看观音。”
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一起同窗那么久了,其实感情不只是结拜兄弟友情同学那么简单的。对于自己其实是女儿身这个事情,祝英台本来是想把这事情说破的,却又没有这个胆量,为此这事总是挂在自己心里,忐忑不定的。
时光飞逝,又过了三个月,已经是三月尾上了,梁祝同窗已经有三年的光景了。
祝英台闲来无事,正在后门口散步。
这个时候,尼山书院的夫子周士章在他们住的地方过去叫了梁山伯,要商量以后学子应考的事情。
银心走进去南院位置,进去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住的房间,叫唤道:“梁相公,周夫子叫你过去呢。”
梁山伯听了,走出门对祝英台说:“夫子叫我过去。”
祝英台点了点头,看着梁山伯出门去找周士章。
梁山伯刚走没一会,忽然走过来一个人,向祝英台施礼,口称相公。祝英台听声看去,原来是家里的仆人王安,便问道:“你又来了,是家里有信来吗?”
王安回答道:“老安人生病,还请相公快点回去。有信,相公请看,就知明白。”说着,就从怀里取出信来,双手呈上。
古人的寄的信,有一尺多长。还没有信封,一般是里外一卷,把口子糊上。
而仆人王安递给祝英台的信是装在竹简里面的,竹筒的口子用布条盖住,然后用绳子捆扎后涂泥封印。
祝英台接过仆人递过来的信,就拆开捆绑的绳子,取下盖好的布条,把信取出来一看,信里果然说是母亲病了,要她赶快回家探望。
祝英台问道:“你知老安人生的是什么病吗?”
王安说道:“我只知道病了,就是睡在床上。什么病,信上想必有写明。”
祝英台手里拿着信,想起来当初启程准备去读书之前,父母再三交代,如果父母生病,就要立刻回家看望。不管真的生病还是假的生病,回家是无可推诿的。再说了自己,留学已经三年了,也是应该回家里去看看了。
想到这里,祝英台于是向王安道:“好,我就回去。但是我还得料理料理行装,到了早明日动身,你看如何?”
王安说道:“但凭相公。”
祝英台说道:“还是你挑一些担子先走吧,明日我和银心随后就跟着。”
王安回答说好的。祝英台让他休息,匆匆回来,碰见了银心,于是告知此事,叫她今天收拾好东西。
银心对祝英台说道:“公子,老爷夫人要我们快回去吗?”
祝英台回答说道:“要回去,你收拾好东西。只是心中有许多不舍。”
银心说:“银心知道,公子是舍不得梁公子。”
“这一别,再难相聚了。”
交代这些事情后,祝英台进了屋来,而梁山伯也刚好从夫子那里回来房间里了。
这个时候,梁山伯正襟而坐,在长案上看书。
这个时候,祝英台看了看梁山伯的背影,心里感到难过,无可形容。于是走近书案旁,站定了脚,眼睛对梁山伯看了看,便说道:“梁兄。”
梁山伯闻言,把书放下,抬头问道:“贤弟有什么事?”
祝英台说道:“你我来尼山书院攻读学习,于今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