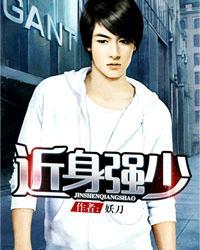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济公传奇52集在线观看 > 第709章 马家再逼祝英台(第1页)
第709章 马家再逼祝英台(第1页)
却说当大家都去送亡人入棺的时候,祝英台大叫梁兄,已经哭晕了过去。
三个女客连同银心都在旁边,立刻把祝英台抱到一旁的椅子上,用手按摩祝英台的太阳穴,好一会儿,祝英台方才回过气神过来。一个女客连忙去斟了一碗热水,让她张开口来,轻轻地灌下。过了一些时候,祝英台哭道:“梁兄呀!”
这时,堂屋里的人,也晓得具体情况。高氏连忙挤了向前走来,擦干眼泪,劝道:“贤侄女,你可别太悲伤了。今日还有一百多里路程要赶呢。”
祝英台问道:“亡人已经入棺了吗?”
高氏答道:“山伯已经入棺了。他的命薄,你就不去想他也罢。”
祝英台说道:“侄儿应当祭奠一番,不敢多耽搁,祭毕,马上就走,银心,我那包袱呢?”
银心道:“下车的时候,我已经交给王安了。”
祝英台的眼神空洞而迷茫,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心死绝望般地说道:“那包袱里面,有白纸两卷,是我自己的诗稿,你给我拿来。这诗稿是在余杭读书的时节,梁兄曾亲自批阅的。于此如今,已经完全变了,我从今以后也不作诗了。”
银心也不敢多说,自己去向王安拿稿子去。
祝英台转而对梁山伯的母亲,说道:“伯母,堂屋里收拾好了没有?”
高氏刚才看见祝英台虽哭晕过去了,已经醒过来。担心会有什么岔子,不敢久留。便说道:“贤侄女,礼堂已经收拾清楚了。”
祝英台便走了出来,只见灵柩头边,摆了桌案,桌案前铺了拜席,案上摆着陶器、铜器作的五供,插着大烛。除了晚辈磕头之外,平辈只奉一揖,长辈只发声长叹,所以礼堂上也极为冷淡。
她走来,对拜席跪了下去,掉了眼泪道:“梁兄,祭奠已毕,马上回去,不能过久耽搁,但愿英魂常在明心阁楼之外,风雨晦明,我哭奠我兄吧。”
说毕,叩完了头。银心已将诗稿取到,祝英台爬起,接过了诗稿,在烛上烧了。祝英台一边烧诗稿,一边说道:“祝英台将所有稿子,在梁兄的灵前烧了,上面有梁兄的评语,同心之言,就此完结,祝英台从此不作诗了。”
等到诗稿烧完了,祝英台对旁边的四九说道:“四九,我的车在门口预备了吗?”
四九在堂前答应道:“我让过来的人,现在备好了。”
祝英台走过来和高氏深深道了万福,执着高氏的手道:“伯母,我走了,尚望你老人少抱悲哀。”
高氏点点头。祝英台回头向灵柩看了一看,点头道:“梁兄,小妹走了。”
说罢,便又哭起来。
高氏劝道:“贤侄女,不能哭了,车子在门口等候了。”
祝英台掏出了手绢,揩了一揩脸,向在堂里的人,都告了别,然后走向大门外。高氏送到她们到大门口来。
高氏说道:“贤侄女,我就不派四九送了。”
祝英台答道:“一路有两个男子,自然用不着人送。不过有事的时候,还希望派四九前去。老人家保重。”
梁家老安人点点头。祝英台上了车,银心跟着上车。她看见四九站在树荫底下,手摘树枝,可是两只眼光,却跟最后一位女客送上牛车了。
晋朝士大夫家,出门一般总是坐牛车的,这是有一些缘故的。魏晋名士爱牛车胜于骑马,或与其身体状况有关。《颜氏家训·涉务篇》亦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这一时期,不少世家子弟常年酗酒、服药,日日莺歌燕舞,导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因为如此情形,别说骑马,就连走路都是一大难题。因为牛拉的车虽然不快,但是稳当。但是在这里,作者为了凸显祝英台焦急想去见梁山伯的心情,所以写了她乘的是马车。再说了,虽然当时流行牛车,也不见得所有士族子弟都用牛车吧?
毕竟普遍用牛车,不代表没人用马车。汉朝初期,抑制商业,视商人为贱者,就规定他们不许乘坐马车。
考古资料表明,秦汉时期的马车车厢很小,人坐在其中,须得正襟危坐。而牛车不仅拥有更大的空间、更齐全的设施,还十分平稳、少颠簸,符合魏晋名士优哉游哉的闲适雅趣。这样一来,牛车就在士人群体中流行了起来。
虽说当时流行牛车,但是仍然有人乘坐马车的。
话回正题,祝英台拜祭梁山伯后,就要和银心回祝家庄了。祝英台坐了马车,车夫说声走,便离了梁家,王安则是骑了马随着走。直到离家不远,祝英台才下了车,换上了便服,再上车往家里来。到家也有二更多天了,祝公远虽然看到祝英台泪痕满面,这也自在意中,只要女儿回来了,那些在梁家哭倒等事,也只好不问。
祝英台回房中安歇,足有个对朝。次日早晨起来,漱洗已毕,只是在房中闷坐。一连三日,尚是如此。
银心劝道:“这样闷坐,终究不是个办法,还是到楼上去看看书吧。”
祝英台叹道:“书也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