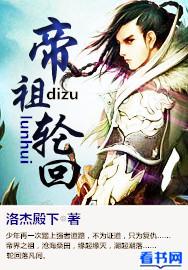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腹黑书生与笨蛋狐狸在线阅读 > 客店(第1页)
客店(第1页)
戎吉虽不太听得懂他的奉承,却也有些不好意思,情不自禁就想挠头,可伸手又觉察自己早黏了许多羊油在手上,于是向陈隐歪头一笑道:“我头痒,你帮我抓一抓!”
他方才同蛇妖恶斗了一场,弄得发髻散乱,此刻正饿死鬼投胎一般地忙着吃东西,头也顾不得梳,顶着一脑袋乱毛,伸手抓着一大块羊肉,露出嘴里的小尖牙用力撕咬,竟有些形如小兽。
孙员外本想说唤个内房中的丫头出来,好好帮这位小公子梳梳头。但见这少年举止如此不类常人,又深知他是有些法力在身上的,一时倒不敢造次了。
这略一迟疑,陈隐便已起身站到戎吉身后将他的头发轻轻拢束起来了。戎吉的头发极多极细,握在手里时软软的一大捧,陈隐觉得这触感似曾相识,倒好像他从前养的那只白狗的大尾巴一般。
孙员外从旁且看他二人,一个忙着抓肉吃浑不在意,一个站在身后帮忙梳头,嘴角还微微翘起,好像是件什么很高兴的事,两人之间竟酝荡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亲昵感,便决定不再多话,只轻轻嗽了一声,朝陈隐笑道:
“自从当日子初贤弟中了茂才,同愚兄约也有两年未曾相见了,这一回是特意赏光来鄙宅喝喜酒,还是要往别处高就?”
陈隐帮戎吉扎好了头发,复又落座,笑道:“岂敢,照理令郎这样大的喜事,是该特意道贺的。只是学生常年居于陋野荒村,不常到县里来,路经贵宅才听说有这等大喜。原本此次是入省城去参加乡闱的,而我这位小兄弟……呃,名唤戎吉,他乃要去省城寻亲,故此同路。”
陈隐两年前考中秀才,乃是本县第一名,他一个无父无母之人,能力压一众乡绅子弟拔得头筹,也很是轰动过几天的。这姓孙的财主又是个爱才的,很是看中陈隐,当初资助过他些盘缠银子,甚至还动过聘他当西宾的念头,故此有些交情。
戎吉对他们这满嘴你来我往的客套没什么兴趣,低着头只顾闷吃,不一会儿已吃得满嘴流油,然后他还很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拍拍肚子道:“好吃好吃!吃撑住了!”
陈隐略觉得尴尬,孙员外也不敢多说,只是赔笑道:“看来鄙舍的厨子倒还有些微末小技,小神仙勉强能入口就好。”
一时二人吃了饭,便要上路,孙员外携妻带子千恩万谢送出大门外,拱手道别不提。
戎吉吃得饱了,心情便十分之好。他从路旁采了朵野花衔在嘴里,一路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儿,负着手在秀才身前一蹦一跳地走,时不时还回头歪过脑袋来朝秀才这边瞅,似乎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跑太快,把秀才给弄丢了。
陈隐心想,这倒像只吃饱喝足后心满意足撒欢儿的小兽,假如他就此躺下来在草地里晒个太阳,怕还会翻过肚皮来叫自己给他挠痒痒。
他暗暗思忖,听口音戎吉也是本地人士,他这样憨吃闷睡一副不知人间疾苦的模样,又有那样一位出手凌厉、衣着考究的叔叔,可见绝非普通小门小户家出来的孩子。可自己祖祖辈辈都住在此地,怎么从没听说过附近还住着这样会降妖的家族?
两个人出了县城,又走上半日,前头闪出一个小村镇来。陈隐在这条路上往来过多次,知道这处叫柳木镇,虽此离县城并不太远,此刻天色也未擦黑,但再往北走下去就都是荒村野地了,便唤住戎吉道:“我们今天晚上就住这里罢!”
戎吉跳过来,抬头很认真地看了看街边小客栈挂出来的一道酒幡:“这一家?”
“就这一家,先吃饭,晚上也在这里歇脚。”
戎吉听说又有饭吃,兴高采烈地应道:“好!”
两个人一径进去,寻了个临窗的位子坐定。戎吉好动,将那扇小小的窗隔往外一推,外面是几亩连着片的池塘。江南四月,正是草长莺飞的好节气,天光尚未暗下来,几个渔家少女撑着长长的竹篙,驾着扁舟在初长了新叶的荷叶上来来往往,遥遥地还能听见她们清脆的笑语晏晏。
戎吉把下巴枕在窗隔上,远远地盯着她们瞧。陈隐见如此,以为他少年天性,遇着天真烂漫的小姑娘难免心向往之,于是笑道:“戎吉家中可有姊妹?”
戎吉原本望着湖面出神,听他作此问,偏过头来瞧了陈隐一眼,不知怎的,那眼神儿里看出点小小的幽怨来:“你问这作甚?”
“倒不作甚,我只是想戎吉你生得可爱,家中若有姊妹,想必都是美人。秀才我也已是弱冠年纪,家中并无妻室,你看我此番上省城考试,若中了举人,你将家中未出阁的姊妹介绍给我一个可好?”
戎吉听了,重重地哼了一声,复又扭过头去看向湖面,道:“我没有姊妹!”
说着,他又微扬起了下巴,口吻里带点炫耀似地说:“但我有舅舅!”
陈隐也闹不明白,问他家里有没有姊妹,怎么就扯到舅舅头上来。何况家中有舅舅,又算什么得意的事?难不成这舅舅竟是个美人儿,比家中那未出阁的如花美眷还高明几分?这没头没尾的,也不好多问。
此刻还未到饭点,店家是个老头儿,原本正在灶下煮米,见来了客人,慢吞吞地上来帮他们倒了两杯热茶,又笑道:“客人是打尖还是住店?今天不巧,正没好东西下饭!”
陈隐道:“不妨事,店里有什么就吃什么。今晚就住在这里,烦请烧一锅热水,我们走得累了,要烫烫脚。”
店家应了一声,不一会儿端出一碟茴香豆,一碟烘好的新笋干来,还盛出两大碗雪白喷香的粳米饭,笑道:“年下腌的咸鱼鲞还有一条,也帮客人蒸了吧?”
陈隐笑道:“蒸来,一发算钱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