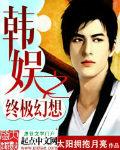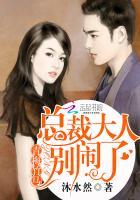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济公传奇片头曲 > 第647章 蔡谟抗谏 李寿改元(第2页)
第647章 蔡谟抗谏 李寿改元(第2页)
随后颜含对别人说:“我听说讨伐一个国家不问仁人,有人问佞于我,难道我有邪德吗?”随即上表辞官,退归琅琊故里;再历二十余年,安然殁于家中。表明高尚。
惟庾亮既反对王导,又欲窃名邀誉,借着北伐的虚声,张皇中外。因特援举不避亲的古义,把两个弟弟登诸荐牍,一是临川太守庾怿,谓可监督梁雍二州军事,使领梁州刺史,镇守魏兴;一是西阳太守庾翼,谓可充任南蛮校尉,使领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再请授征虏将军毛宝,监督扬州及江西诸军事,与豫州刺史樊峻,同率精骑万人,出戍邾城。然后调集大兵十万,分布江淝,由自己移镇石城,此非江南之石头城,乃在淝水左近。规复中原,乘机伐赵。
表文上面,说得天花乱坠,俨然有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状态。其实只是做画饼充饥。
晋成帝司马衍阅览到庾亮的文表,也不禁怦然心动,于是将表文颁示给朝廷各大臣,令他们议复。
太傅王导,是朝中领袖,且又得晋成帝诏命,升任丞相。这番军国大事,当然要他首先裁决,王导看了表文,掀髯微笑道:“庾元规能行此事,还有何说,不妨请旨施行。”言下有不满意,实是请君入瓮。
太尉郗鉴接口说道:“我看是行不得的,现在军粮未备,兵械尚虚,如何大举?”也是忠厚人的口吻。
此外百官,亦多赞成郗鉴的建议。太常蔡谟,更是发出一篇大议论,作为议案,文如下:
盖闻时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虽终灭亡,然当其强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屈于巴汉,忍辱于平城也。若争强于鸿门,则亡不终日,故萧何曰:“百战百败,不死何待也。”
原始要终,归于大济而已,岂与当亡之寇,争迟速之间哉?夫惟鸿门之不争,故垓下莫能与之争。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勾践见屈于会稽,故威申于强吴。今日之事,亦犹是耳。贼假息之命垂尽,而豺狼之力尚强,为吾国计,莫若养威以待时。时之可否,系于胡之强弱,胡之强弱,系于石虎之能否。
自石勒举事,虎常为爪牙,百战百胜,遂定中原,所据之地,同于魏世,及勒死之日,将相欲诛虎,虎独起于众异之中,杀嗣主,诛宠臣,内难既定,千里远出,一举而拔金墉,再举而擒石生、诛石聪,如拾遗,取郭权,如振槁,还据根本,内外平定,四方镇守,不失尺土。以是观之,虎为能乎,抑不能也?假令不能者为之,其将济乎,抑不济也?贼前攻襄阳而不能拔,诚有之矣,但不信百战之效,而徒执一攻之验,譬诸射者百发而一不中,即可谓之拙乎?且不拔襄阳者,非虎自至,乃石遇之边师也。
桓平北桓宣为平北将军,见前。守边之将耳,遇攻襄阳,所争者疆场之土,利则进,否取退,非所急也。今征西指庾亮。以重镇名贤,自将大军,欲席卷河南,虎必自率一国之众,来决胜负,岂得以襄阳为比哉?今征西欲与之战,何如石生?若欲守城,何如金墉?欲阻淝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苏峻?凡此数者,宜详较之。石生猛将关中精兵,征西之战,殆不能胜也。金墉险固,刘曜十万众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殆不能胜也。又当是时洛阳关中,皆举兵击虎,今此三镇,反为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势也。石生不能敌其半,而征西欲当其倍,愚所疑也。苏峻之强,不及石虎,淝水之险,不及大江,大江不能御苏峻,而欲以淝水御石虎,又愚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谯,田于城北,虑贼来攻,预置军屯以御其外。谷将熟,贼果至,丁夫战于外,老弱获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烧谷而走,如此数年,竟不得其利。是时贼唯据淝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扞其一,而征西欲御其四,又愚所疑也。或云贼若多来,则必无粮。然致粮之难,莫过崤函,而石虎首涉此险,深入敌国,平关中而后还。今至襄阳,路既无险。又行其国内,自相供给,方之于前,难易百倍,前已经至难,而谓今不能济其易,又愚所疑也。
然此所论,但说征西既至之后耳,尚未论道路之虏也。自淝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泝流,首尾百里,若贼无宋襄之义,及我未阵而击之,将如之何?今王师与贼,水陆异势,便习不同,寇若送死,虽开江延敌,以一当千,犹吞之有余,宜诱而致之,以保万全。若弃江远进,以我所短,击彼所长,惧非庙胜之算也。鄙议如此,伏乞明鉴?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篇长篇大论之文,表示大众,没一人敢与他批驳,就是呈入御览,晋成帝亦一目了然,料知北伐是一种难事,于是下诏令庾亮停止北伐,不必移镇。
咸康五年(339年),郗鉴病重,将府中事务交给长史刘遐,上疏请求辞职,疏文有云:
臣疾弥留,遂至沈笃,自忖气力,不能再起,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过才,曾无以报,上惭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叹,抱恨黄泉。臣今虚乏,危在旦夕,因以府事付长史刘遐,乞骸骨归丘园,惟愿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济大猷,任贤使能,事从简易,使康哉之歌,复兴于今,则臣虽死,犹生之日耳。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以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若当北渡,必启寇心。太常臣谟,平简贞正,素望所归,可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子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是以敢希祁奚之举。
文中祁奚乃是春秋时晋人。郗鉴迫切上闻。这疏文上达朝廷后,不到数日,郗鉴便即谢世,年已七十有一。
郗鉴系高平金乡人,忠亮清正,能识大体,殁后予諡文成,所有朝廷赠恤,一如温峤故事。且依郗鉴遗疏,迁蔡谟为徐州刺史,都督徐兖二州军事,晋朝廷即授郗迈为兖州刺史。
可巧丞相王导,与郗鉴同时起病,先是郗鉴告终,晋成帝特别哀悼,特遣大鸿胪监护丧事,赗襚典礼,仿诸汉博陆侯霍光,及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予諡文献。
王导卒年六十有四,当时号为中兴第一名臣。
晋成帝征庾亮为丞相,庾亮复上表固辞,于是进丹阳尹何充为护军将军,庾亮弟会稽内史庾冰为中书监,领扬州刺史,充并参录尚书事。
当时庾冰受到朝野寄予厚望,庾冰上任后亦不分日夜处理政事,而且提拔后进,敬重当朝贤士,时人都他为贤相。及后庾冰又整理户籍,查出万多名本记录的人,充实人口,增加军资供应。
庾冰胜过乃兄。独独庾亮尚欲北伐,又想申表固请,适而接到邾城失守的警信,方不敢再提北伐二字。
邾城虚悬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真是孤危得很。从前陶侃在日,镇守武昌,僚属屡劝侃分戍邾城,陶侃乃引集将佐,渡水指示道:“此城为江北要冲,差不多是虎口中物,我国家现在势力,只能保守江南,倚江为堑,阻住戎马,若出守此城,必致引虏入寇,非但无益,反且有损。我闻孙吴御魏,尝用三万兵扼守此城,今我兵不过数万,怎能分顾?不若弃为空地,省得夷人生心,我却好安守江南,尚不失为中策呢。”
将士兵佐因陶侃说得有理,当然无言,于是随陶侃渡江回镇。陶侃既而去世,由庾亮代任,庾亮视邾城为要地,谓可借此进兵,于是使毛宝、樊峻,前往把守邾城。果然被赵主石虎闻知,立刻派遣大都督夔安,带领石鉴、石闵、李农、张貉、李菟等五将,分率五万人,进军攻打邾城。
毛宝忙向庾亮求救,庾亮反而视若无事,不急前往援救,终究导致邾城陷没。
毛宝与樊峻突围出走,为赵兵所追,俱投江溺死。夔安又转而攻陷淝南,连拔江夏义阳等郡,进围石城。还亏竟陵太守李阳,发兵掩击,方才得破赵兵,斩首五千余级,才将赵兵杀退。
庾亮始终不敢渡江,但上表谢过,自愿贬降三等,权领安西将军。有志北伐者,果然如此?有诏免议,惟庾怿为辅国将军,领豫州刺史,监督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镇守芜湖。
庾亮自邾城陷没,忧慨成疾,咸康六年(340年)正月初一,庾亮旋即殁世,享年五十二岁,追赠太尉,諡曰文康,晋朝廷进升护军将军何充为中书令,命南郡太守庾翼为安西将军,领荆州刺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代替庾亮镇武昌。
当时人怀疑庾翼年轻,不能继承他兄长庾亮的业绩。但庾翼尽心治理,军务和政务都很严明,数年之间,官府和私人资用充实,众人都称赞他的才能。
惟庾翼志大言大,好谈兵事,既欲灭赵,又思平蜀,仍不脱阿兄气习。因而通使燕、凉,拟与和好,倚为外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