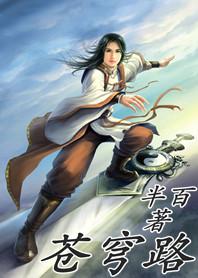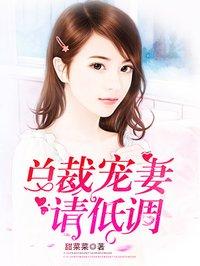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济公传奇片头曲 > 第666章 海西公被废 昆仑子承基(第2页)
第666章 海西公被废 昆仑子承基(第2页)
还有广州刺史庾蕴,太宰长史庾倩,散骑常侍庾柔,皆为前车骑将军庾冰之子,就是废帝司马奕的皇后庾氏的弟兄。庾后既连带被废,降为东海王妃,桓温恐庾家族大宠多,暗中图划报复,于是想出一法,先扳倒武陵王司马曦,诬告他父子为恶,曾与袁真同谋叛逆,因此即免官归藩。
晋简文帝不得不从,出司马曦就第,罢司马曦之子司马综和他等官。桓温又迫令新蔡王司马晃,诬罪自首,连及武陵王司马曦父子,并殷涓、庾倩、庾柔等人,一同谋逆,且将太宰掾曹秀,舍人刘强,凭空加入,一股脑儿收付廷尉。
御史中丞谯王恬,即谯王承之孙。暗承桓温旨意,请依律诛杀武陵王怛。
晋简文帝复诏道:“悲惋惶怛,非所忍闻,应更详议。”
桓温复自上一表,固请诛曦,语近要挟,简文帝手书给桓温,内有晋祚未移,愿公奉行前诏;若大运已去,请避贤路云云。
桓温览到此诏,也不觉汗流色变,始奏废曦及三子家属,皆徙新安郡,免新蔡王司马晃为庶人,徙锢荥阳。殷涓、庾倩、庾柔、曹秀、刘强,一律族诛。
简文帝不便再驳,勉依桓温之议,可怜殷庾两大族,冤冤枉枉死了若干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庾蕴在广州任内,闻难自尽,庾蕴长兄前为北中郎将庾希,季弟会稽王的参军庾邈,及庾希子攸之,并逃往海陵陂泽中。
独东阳太守庾友,也是庾蕴的兄长,因其子妇为桓温从女,特邀赦免。桓温自是气焰益盛,擅杀东海王司马奕三个儿子,及田氏孟氏二美人。旋复奏称东海公废黜,不可再临黎元,应依昌邑故事,筑第吴都。
晋简文帝商量诸多政治层面的事情,然后请褚太后下令,谓不忍废为庶人,可妥议徙封。
桓温复上奏说可封司马奕为海西县侯,于是朝廷有诏徙封司马奕为海西县公。废后庾氏,积忧病殁,尚追贬为海西公夫人。会吴兴太守谢安,入为侍中,遥见桓温面色,便即下拜。桓温惊呼道:“安石。何故如此?”安石就是谢安的表字。
谢安答道:“君且拜前,臣难道敢揖后吗?”
桓温明知谢安有意嘲讽,但是自己素来看重谢安名望,不便发作,且默记前时女尼对自己的微言,也有戒心,因此即上书鸣谦,求归姑孰。
朝廷诏进桓温为丞相,令居京师辅政。桓温仍然固辞,乃许他还镇。
秦王苻坚听闻桓温行废立之事,顾语群臣道:“桓温之前败灞上,后败枋头,不知思愆自贬,遍谢百姓,反且废君逞恶,六十老人,作此举动,怎能为四海所容?古谚有云‘怒其室,作色于父’便是桓温的注脚呢。”
桓温虽然还镇,揽权如故。且留郗超为中书侍郎,名他为入值宫廷,实是隐探朝事。
晋简文帝格外拱默,尚恐桓温再有异图,此时,天文师见荧惑星逆行进入太微星旁边,上报朝廷,晋简文帝越发感觉惊惶,原来皇帝司马奕被废以前,荧惑星曾经守太微端门,仅逾一月,即有废立大事。此番又经星文告变,哪得不危悚异常。晋简文帝当下召来郗超,问道:“命数修短,也不遑计,但观察天文,得勿复有前日事么?”
郗超答道:“大司马温,方思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事只可一为,何至再作?臣愿百口相保,幸陛下勿忧!”
晋简文帝说道:“但得如此,尚有何言!”
郗超即告退。侍中谢安,曾经与左卫将军王坦之,来到郗超身边禀告事情,郗超门多车马,络绎不休,待至日旰,尚未得间。
王坦之欲离去,谢安秘密对他说道:“君独不能为身家性命,忍耐须臾么?”
王坦之于是忍气待着,直至薄暮,才得与郗超清谈,言语说毕就告别了。
郗超之父郗愔卸职家居,偶有不适,由郗超请假归省,晋简文帝与语道:“致意尊翁,家国事乃竟如此,自愧不德,负疚良深,非一二语所能尽意。”
说至此,因而咏昔人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二语本庾阐诗。咏罢泣下,郗超无言可对,拜别而去。好容易过了残年,复遣王坦之征桓温入宫辅佐,桓温复固辞,惟与王坦之言及,请将海西公外徙。
王坦之返报,乃徙海西公至吴县西柴里。敕吴国内史刁彝,就近防卫,并遣御史顾允,监督起居,免有他变。
蓦然听闻庾希和庾邈,联结故青州刺史武子沈遵,聚众海滨,掠得鱼船,夤夜突入京口城。晋陵太守卞耽,猝不及防,逾城奔曲阿,于是建康震惊,内外戒严。嗣又得庾希等檄文,托称受海西公密旨,起诛首恶桓温,累得京畿一带,讹言蜂起,益相惊扰。
平北参军刘奭,高平太守郗逸之,游军督护郭龙等,引兵往击,就是卞耽,亦调发县兵,一并讨发庾希等人。
希众统是乌合,一战即败,闭城自守,再由桓温遣到东海太守周少孙,也有锐骑数千,合力攻城,攀堞杀入。庾希兄弟子侄,以及沈遵等人,没处逃奔,遂致陆续被擒,送到建康市中,伏诛了案。一番乱事,数日即平,晋廷诸臣,入朝庆贺,又像是化日光天。冷隽之语。
哪知吉凶并至,悲喜相寻,晋简文帝忽然得病,医治罔效,差不多将要归天。当时皇后太子,俱尚未立,说将起来,又须溯述源流,表明颠末。
晋简文帝为晋元帝之少子,生母郑氏,受封建平国夫人,咸和元年病殁。晋简文帝受封主爵,追号郑氏为会稽太妃,嗣位后时日尚浅,故未及追尊。
惟晋简文帝先娶王氏,生子司马道,生为世子,后来母子并失帝意,俱被幽废,王氏忧郁成疾,亦即去世,此外妾媵颇多,生有三个男孩,又皆夭逝。
未几,司马道生又亡,晋简文帝年垂四十,迭丧诸子,未免悲悼,况膝下竟致无男,诸姬偏皆绝孕,不由的寸心焦灼,百感旁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