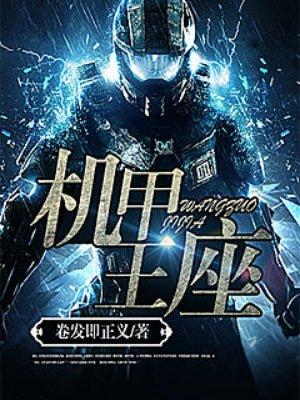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济公传奇片头曲 > 第706章 楼台会相诉断魂(第5页)
第706章 楼台会相诉断魂(第5页)
话没说完全,梁山伯一阵不住地咳嗽,他连忙在身上将一条白罗手绢取出来,两手捧住,紧紧的握住了嘴。身后有一只圆墩,梁山伯就坐了下去。低了头,弯着腰,两只手握住堵嘴的手绢,不住地咳嗽。
这个时候,祝英台看见梁山伯手里的白色绢子上面有着点点红色的散状的点,忽然哎呀了一声,然后说道:“梁兄,你手绢上面,怎么许多的红点,不要是吐红了吧!”
梁山伯没有作声。
祝英台弯腰将梁山伯手里的手绢抢了过来,打开一看,手绢的正中只见一团鲜血在上面,而且这手绢四五层都湿透了。祝英台抖着手绢,眼眶泛起涟漪,哀伤说道:“哎……,兄……,你果然口吐鲜血呀?是小妹将你害了。”
梁山伯有气无力的说道:“不要紧,这是心头烦闷,一时咳嗽失红,过一会就好了。”
祝英台把梁山伯那只手绢放在桌子上,把桌子上银心送来的一碗菜汤,双手捧着递到梁山伯的面前。语气万般温柔地说道:“梁兄,请漱漱口。”
梁山伯因碗在祝英台的手上,看了她,说道:“生受你了。”
梁山伯因而对碗喝了两口,漱了口,把桌上放的手绢取了过来,将水吐在上面,桌子上面的手绢拿起来,然后把手绢折叠着手里捏着,站了起来,对祝英台说道:“我在这里,可不能病倒了,这真是要走了。”
祝英台放下碗,好一会时,才点点头,说道:“梁兄,我送你一程,尽一尽……。”
她话未曾说完,眼睛再也包不住眼泪,仿佛抛砂一般,只管往下滴落。祝英台站在明心阁匾下,抬起一只袖子,只管揩泪。
梁山伯叹口气道:“我一路奔来,真个汗如雨下,但是为了要见贤妹,均不计较。如今啦……。”他摇摇头,说着,迈步下楼。
祝英台怕他跌倒,步步跟随,因而道:“我每日在楼上看书,每次听到脚步响,总以为梁兄前来。如今望得我兄前来,却这样吐红回去,可怜!无奈!”
梁山伯回道:“但愿贤妹时时念着愚兄。”
四九和银心都在楼下,看见梁山伯手扶了墙,一步挨着一步走。祝英台随着人下楼,已哭得泪人儿似的。两人都吃了一惊,异口同声叫了一句相公。
祝英台嘱咐道:“银心,你把我的马,备好鞍子,牵到门外,送梁大相公他们回去?”
银心听了,答应说是,赶快去马棚里去牵马了。
梁山伯向祝英台望了望,拱拱手道:“不必送了。”
祝英台揩了揩眼泪,也是目光看着梁山伯,道:“望兄回家,好好休息,好了,还望再来。”
梁山伯回答道:“若并无大病,自然还是要来见你。可若是病体加重,怕我会短命,到那时就不能前来了。”
说时,梁山伯和祝英台已经走出楼底下,偏西的太阳,照见楼下的柳树树荫,有半个院子大的树影,已向东移。
祝英台站在柳树荫下,因而道:“梁兄何必出此不幸之言。万一不幸,在甬江岸旁,有个高桥镇,是我两人千秋歇足之地,就在这里埋下两道碑,一块碑上写着梁山伯,一块碑上写祝英台,我……。”这个时候,祝英台已经泣不成声了。
梁山伯本来候着银心牵马,听听门外可有马叫。听了祝英台这话,猛然的一惊,问道:“高桥镇若是我两人千秋歇足之地,贤妹也愿意去?”
祝英台答道:“我已说了,暗下定了非兄不嫁,虽死不改。梁兄若定了高桥镇为千秋歇足之地,妹决计前去,与兄共冢。”
梁山伯点头道:“贤妹此言,不可太过,人各有命,何苦连累贤妹?你我今生如果不能连为姻缘,那是福运不够吧。是愚兄福薄。贤妹当今要如此?”
祝英台定了定心神,说道:“事事难说,梁兄也不用太失望。情之深能动天感地,也未可知呀?搜神记里有个故事,梁兄可知?”
祝英台徐徐说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位的时候,有个叫王道平的长安人。少年时代,他就和本村唐父喻立誓结为夫妇。不久,王道平应征去打仗,流落在南方,九年不能回家。唐父喻的父母看到女儿已长大成人,就把她许配给刘祥做妻子。唐父喻因为与王道平立誓,所以不肯嫁。父母强迫她,她设法逃避,就嫁给了刘祥。这样一直过了三年,她整天精神恍惚,闷闷不乐,常常思念王道于,悲忿愁怨极深,忧郁地死了。唐父喻死后三年,王道平回到家中,了解到唐父喻已死,就到她的坟墓痛哭,并连连呼唤唐父喻的名字,结果唐父喻的灵魂就从坟墓中出来,告诉王道平挖开坟墓,撬开棺材,自己就可以复活了。王道平按照她说的做,唐父喻果然复活了,于是两人回家了。唐父喻的丈夫刘祥,得知这件事,就向衙门申诉,要求领回唐父喻。州县官员看到法律上没有相应的条文,便把这情况上奏至秦始皇帝。当时的秦始皇听说这个事后,叹道:“此乃至情动天地。”于是就下令把唐父喻判给了王道平做妻子。据说后来王道平活到一百三十岁。”
梁山伯听到祝英台说起这个故事,有点感到哭笑不得地说:“贤妹信这个故事?”
祝英台说:“信又何妨,既然有人记录这个故事,那自然有那写书的人的一番道理了。到时,说不定我也像那个王道平一样,把你挖出来,你活过来了呢?”
梁山伯听了祝英台这样说,于是回答道:“如果贤妹真执意如此,愚兄到时命终,当叫家人把我安葬在高桥镇,立下两块碑,尽等妹来。”
祝英台和梁山伯说到此处,英台已经泪如雨下,只是点头。
四九自祝家庄的屋里走出来,对梁山伯说:“相公,回我们去吧,你的身体不好得很呢?”
梁山伯向祝英台一揖,说道:“贤妹,我走了。”
祝英台回了一个万福。梁山伯抽转身来,向大门口而去。
祝英台唤道:“梁兄呀,等等……。”
那柳树枝被乱风一吹,齐向东来,挡住望远的人目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