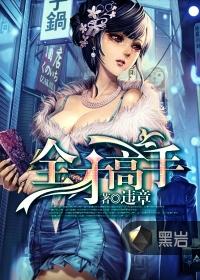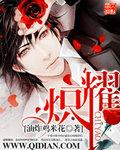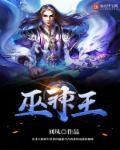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济公传奇片头曲 > 第712章 法显西行取经年记(第1页)
第712章 法显西行取经年记(第1页)
法显本姓龚,出生在平阳郡,早年便见证了后赵、冉魏、前燕和前秦势力的相互取代。他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岁左右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
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
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和尚进入成年后,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已在佛教界度过了六十余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
法显为此感到非常忧虑,有一日,法显和尚游览华山的时候,遇到了在东汉时期就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宝掌和尚。据说宝掌和尚是中印度婆罗门贵族的儿子,出生时间相当于我国战国时期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公元前414年)七月七日午时出生的人,在东汉末期桓帝之初的建和至永兴年间(公元1—153),从尼泊尔进入中国,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
法显看见眼前这个僧人,目光睿智犀利,料想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修为的高僧。于是询问法号,宝掌和尚让他称呼自己为宝掌就好了。
法显出家多年,也是听说过宝掌和尚的名号的,只是没有亲眼见过他本人。而且又据说他是周朝时期的人,到现在少说也得有七百多来年了,他虽然信仰佛法,但是对这个传闻还是保留一些怀疑的。
直到现在,亲眼看见这个西域僧人自称自己是宝掌和尚,他心里就疑惑了很多了。
宝掌和尚,住世界多年,自是得道修有一些神通,而他心通是能知三界六道众生心中所思所想之事。
此时,宝掌和尚自然是知道法显和尚心中的疑惑,于是回答道:“这位道友,心有疑惑,谓世间如何有活了几百岁之人?以为传闻的宝掌和尚乃是民间百姓杜撰,或有其人,但其人无此长寿乎?道友本姓龚,自小出家,也有六十年之春秋。”
法显和尚听了西域僧人宝掌说的话,方才相信眼前乃是得道高僧,并且是名副其实的宝掌和尚,传闻他前身愿力:要在人间住世千年。
法显和尚连忙合掌行礼,道:“小僧多有冒犯高人。”
宝掌和尚示意他随自己找了棵大树,在大树下,两人面对面坐下来交谈。
宝掌和尚直接就对法显和尚说:“道友心有烦恼,谓如今佛法传到华夏,经典不全,僧人戒律不明,甚至为非作歹,你一心想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有如此心,可谓功德已在法界,福德定在眼前。”
法显和尚说道:“正是,高人道出小僧之疑惑忧愁。小僧不知道如何方能逆转佛教在华夏之困顿。”
宝掌和尚徐徐说道:“早期佛教传播以僧侣迁徙和口传心授为主,佛经的大规模传入发生在汉明帝时期,比如白马驮经事件。但是当时也有四十二章经,经本少,人民得到的指导就少。到了汉桓之初,西域僧人安世高始到中夏,安世高认为应当让人们了解佛教,于是萌发了译述佛经的宏愿。共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但是主要是小乘系的佛经,百姓对其佛经文字还是晦涩难懂。”
法显和尚端正身体,仔细地听讲,不敢打断宝掌和尚的话。
等到宝掌说到这里,法显和尚才说道:“大师所说,意思是从天竺传来的佛经还是太少了。所以佛法在弘扬的时候,仍然有一些弊端。”
宝掌和尚点了下头,接着说道:“佛教建立之初,佛祖释迦牟尼随处说法,并无经书。后面涅盘圆寂之后,弟子感念佛陀教法,为了不使其灭绝法脉,由记忆深广第一的阿难随五百罗汉比丘记录佛陀四十几年所说的教法与比喻,集合为书,是为佛经。”
宝掌和尚又说:“佛陀灭度之后的三个月到往后的四百年里,天竺僧人们一共四次结集佛经,并且分化为小乘、大乘之别,如今的佛经大多数只是小乘之法,而且还是有很多缺少的教理没有说明。佛法广大,贫僧当初来中华之地之前,虽然有在天竺地区阅读过许多佛经,但是毕竟都是梵文,一一难讲,况且文词翻译难免不能让你们华夏人理解。道友若要平息佛门之乱象,只有西行求法,把还没有传到中国的佛经,去天竺国带来,而且佛经之多,别类不同,路途遥远,道友只能选择而带,自然不可能悉数带回。”
法显和尚听了宝掌高僧这番话,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道:“多谢高道指引,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贫僧虽然年老,也要西行求法,取回佛经。佛经广大,这辈子取不完,下辈子我还要去取经,哪怕死到中途,也要让华夏能有正统的佛经佛法,指引众生离苦得乐。”
宝掌和尚听见法显和尚许下如此大愿,道了一句善哉善哉。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而法显和尚乃是西天如来佛祖的座下弟子金蝉子转世,当初他在法会之上打个瞌睡,被金鹏向如来告状,如来于是罚他下凡投胎,为十一世为僧。这一世的金蝉子转世就是法显和尚,到了最后第十一世,就是唐朝的玄奘和尚,也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这是以后之前,暂时不说。
法显和尚得到宝掌和尚的指导,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和尚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次年,他们穿过河西鲜卑人建立的西秦与南凉,到了北凉王段业管理下的张掖(今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组成了十个人的“巡礼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巡礼团”西进至敦煌(今甘肃敦煌),得到敦煌太守李暠的资助,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
法显等五人随使者先行,智严、宝云等人在后。白龙堆沙漠气候非常干燥,时有热风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法显后来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渡过了“沙河”,来到了白龙堆以西第的首个绿洲城市--鄯善。那里也是汉朝时的楼兰故土。居民最早是原始的地中海-阿富汗型印欧人。在北印度的贵霜帝国崩溃后,又多了一群带着犍陀罗语的流亡贵族,因此会看起来兼具东西方特色。
普通人的服饰已大体汉化,仅仅是在衣料上以毛织物或者麻为主。但罗布大泽附近的土地贫瘠,十分严重的盐碱化让产出很少。虽然支撑了灿烂文化,但反复争夺也为这里的原住民制造着巨大苦难。就在法显抵达之前,这个小国还被前凉西征与前秦进攻龟兹所牵连。
接着,他们又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了茑夷国(今新疆焉耆)。本地居民也是典型的印欧人,国号来自于梵语的阿耆尼,也就是印度教中的火神。但同样盛行从印度传来的小乘佛教,并印度的婆罗米字母作为书写系统。虽然国库储备不充足,但是这里的居民能骑善射,所以经常仗着勇力劫掠过往商旅的财富。
他们在茑夷国住了两个多月,宝云等人也赶到了。当时,由于茑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小乘、大乘两大派),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所以他们在茑夷国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在今克什米尔)。
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吕光远征龟兹时留下的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塔克拉玛大沙漠地处塔里木盆地中心(塔里木,在古突厥语中本意为“之流”;塔克拉玛干含义则一直没有定论。一般比较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有三种:1、葡萄之乡;2、原来的家园;3、吐火罗人的家园),这里异常干旱,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变化无常。行人至此,艰辛无比。正如法显所述:“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
这个古老的塞人城邦,同样是东西混血频繁的据点。虽然依然讲伊朗语分支,但与很早西迁的内地军民结合。当地的尉迟氏君王,也使用波斯氏的万王之王头衔,在南疆作威作福。最后兼并了附近的4个小城邦,发展为有8万人口和3万战兵的区域小强。
在本地肥沃的土地和和田河的哺育下,于阗可谓是国泰民安,以至于可以奉养数万僧人。又因为丝路上的商人往来众多,所以寺庙也扮演着当铺、银行、旅店和招待会所等作用。成熟的寺庙经济让僧人有财力传播自己的信仰,并接待来自东土的同道。当地人对大乘和小乘佛法一视同仁,所以法显和尚得到了不错的待遇。
当时正值佛诞节,法显和尚发现于阗王有一尊可以移动的圣象车。上面的佛像披挂丝绸帷幔,并用佛教七宝装饰,还有2个金银铸造的菩萨陪护在左右。在佛像即将进城时,宫女们会从城门上撒下花瓣。王族大臣也会换上新衣,赤脚持花朝拜大佛。这种极具西方古典文明特色的崇拜仪式,无疑让法显和尚印象深刻。
更重要的,僧侣仅仅抵达于阗就已经见到众多闻所未闻的经书抄本。这些内容就足以让他们学习消化很长时间。但法显和尚认为,只有越过了葱岭才能接触到真正的佛法,而不是在西域世界满足于二手货。
队伍接着继续前进,经过子合国,翻过葱岭,渡过新头河到了那竭国。过了葱岭后,法显看到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经过后来十分着名的瓦罕走廊时,他就将寒风和冰川称为毒龙。四季寒冷的气候条件,也是法显所从未所经历的体验。如果没有赶上合适的时间翻山,就容易被大风卷走。石梯大都位于山间,下面就是万丈悬崖。只要行者往下探望,就会失去迈出第二步的勇气。所以,当地只有被称为雪山人的塞种后裔在分散地居住。
但法显和尚还是没有退缩,在强大信仰的支撑下继续前进。漫漫长夜中,瑟瑟发抖的僧侣们都围着火堆,分享各自知晓的佛教经典故事。当然也有汉明帝梦见西天金人的因缘际会,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期待尚未谋面的西方极乐。
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途中,北天竺有一个小小的陀历国,就位于当代巴基斯坦北部的达历尔(darel)地区,信仰小乘佛教。这里有用木头雕刻惟妙惟肖的佛像。在希腊化艺术的影响下,这些早期佛陀造像都是以希腊神祗为原型,其灵感可追溯至古典时代的太阳神阿波罗。
在古典晚期与中世纪前期,整个中亚东部也依旧是古典希腊艺术的保留地。即便是月氏出身的贵霜后裔,也大体遵从这些文化遗存。他们也是佛教东传的主要输出来源。
在斯瓦特河边的另一个小国——乌苌国,法显第一次见识到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婆罗门胡人是当地的统治者,而且精通天文历法和占卜之术。如果遇到了无法裁决的案件,他们就让人服用草药,将先发狂的人定罪。当事人几乎毫无怨言,也绝不反对结果。但这里的国君也不滥用死刑,最严厉的惩戒不过是流放。就和其他古印度国家类似,这里的印度教僧侣待遇好。甚至有专门认路的驴子能将粮食驮到山中寺庙,服务这些不食人间烟火、不沾俗世的婆罗门使用。
公元402年,该年东晋改元元兴,南凉由建和改元弘昌,柔然建立汗国,同时存在后燕、后秦等十余个割据政权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