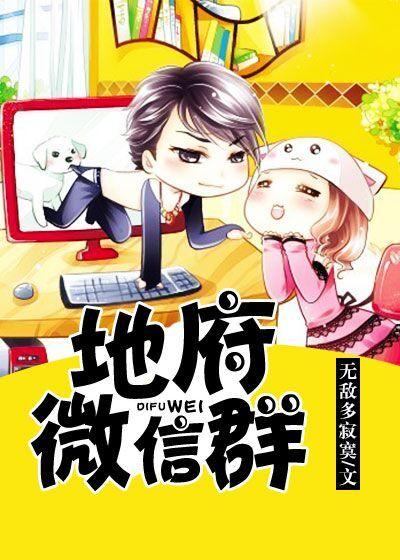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贤名远播的意思 > 第149章 莎拉的诅咒(第2页)
第149章 莎拉的诅咒(第2页)
四个人默默向电梯间走去,迎面碰到一个健硕的女服务员,林梓明停住脚步平静地说:“美女,601房的床单脏了,马上去把它换掉。”
服务员笑着点点头,推着酒店客房工作车走向601房。
徐晓煝和melia狠狠地掐了一下林梓明的屁股,四个人无声地进入电梯。
回到片场,导演满脸笑容,宛如一朵盛开的鲜花,说道:“梓明,你又一次在拍戏现场玩起了‘失踪游戏’,不过这种氛围恰似我电影中最渴求的那一抹神秘色彩。”
“莎拉,你终于回来了,怎么你的衣服好似被撕裂的花瓣,你是没事吧?”阿弥尔汗的眼睛突然如同两颗闪耀的星星,散发出炽热的光芒,他如一只谄媚的哈巴狗般,殷勤地跑过去,想要拥抱莎拉。
莎拉使出浑身力气,如同推开一堵沉重的墙壁,冷冷地说道:“阿弥尔汗先生,请与我保持距离,你身上的咖喱味令我无法忍受!”
“该死的,这朵带刺的玫瑰!待到了印度,我定要用咖喱将你灌醉!”阿弥尔汗紧咬着牙关,眼中闪烁着怨恨的火花,狠狠地瞪着莎拉,仿佛要将她生吞活剥。
旁边的人强忍着笑意,纷纷转过身去,脸上的笑容如同一朵朵盛开的鲜花,难以抑制。
“好了,今日的拍摄堪称完美,大家早些歇息,下场戏我们要远赴北极圈,去捕捉那绚丽多彩的极光身影。”导演声如洪钟,大声地宣布收工。
回到酒店,林梓如同一条灵活的鱼,迅速钻进浴缸,享受着热水的洗礼。
突然,一个可怕的信息传到手机屏幕。他匆忙穿上衣服,如同离弦之箭一般,驾车疾驰向郊外。
(2)
俄罗斯的深秋是场缓慢而盛大的生命轮回。西伯利亚的寒风如钝刀,一层层剥开白桦林的金色皮囊,露出底下惨白的树干,像大地刺向灰蒙天空的肋骨。
车轮碾过厚厚的腐叶层,发出沉闷而粘腻的声响,仿佛碾碎了无数个寂静的黄昏。林梓明开着长城越野车,引擎声在这片无垠的寂静里显得格外粗粝,像一头疲惫的野兽在旷野中喘息。
他停下车,推门而出。冰冷的空气瞬间裹住他,带着针尖般的刺痛感钻入肺腑。
眼前,白桦林无边无际地蔓延,金黄的叶片仍在簌簌飘落,旋转着,覆盖住枯死的蕨类植物和深褐色的泥土。
远处,低矮的山峦线条模糊,被一层薄薄的、带着死亡气息的灰雾笼罩。
一切都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静得能听见时间在这片冻土上缓慢冻结的脆响。
直到那抹红闯入视野。
就在林梓明前方十几米,一棵格外粗壮的白桦树下,站着一个身影。
一件剪裁精良、火红如血的毛呢大衣,在漫天枯黄与惨白中,灼痛了他的眼睛。大衣下摆被风掀起一角,露出笔直纤细的小腿线条。
她背对着他,金色的长发在风中扬起,每一缕都闪耀着不属于这个季节的、近乎虚假的光泽。
“迷路了吗,先生?”她转过身,声音像裹了蜜糖的丝绸,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异域口音。
林梓明呼吸一窒,心底一阵冲动。眼前的女子似曾相识,美得令人心惊,也美得令人不安。
皮肤是毫无瑕疵的冷白,如同上等的羊脂白玉,在暗淡的光线下泛着微光。
五官精致得如同最高超的匠人一笔一划精心雕琢出来,比例完美到失真。
尤其是那双眼睛,湛蓝得如同最纯净的冰川湖水,深处却空洞得可怕,映不出任何倒影,也读不出任何情绪。
她像一个被精心打扮、刚从橱窗里走出来的芭比娃娃,完美,也带着一丝灵魂。
“莎拉,”她主动伸出手,指尖冰凉得不似活物,“莎拉·伊万诺娃。”
莎拉?俄罗斯的美人都叫莎拉吗?
“林梓明。”他握住那只手,那触感光滑、坚硬,仿佛覆盖着一层看不见的釉质,心底深处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寒意。她出现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合理。
“车子……好像出了点小状况。”莎拉微微歪头,指向那棵白桦树后。她的动作带着一种刻意训练过的优雅弧度,如同设定好的程序。
林梓明跟着她绕到树后。一辆线条流畅、价值不菲的银色跑车斜陷在泥泞里,一个后轮深陷在落叶覆盖的坑洼中,底盘几乎贴着湿冷的泥地。这车,这地点,这困境,一切都透着精心设计的荒谬感。
他叹了口气,卷起袖子,戴上防水劳工手套。泥土冰冷刺骨,带着腐烂植物特有的腥气。他费力地搬来石块垫在车轮下,又从自己车里取出拖车绳。
莎拉只是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双手优雅地交叠在身前,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略带感激的微笑,那笑容仿佛凝固在脸上。
引擎轰鸣,绳索绷紧。在车轮卷起的泥浆和腐烂落叶的飞溅中,跑车终于艰难地脱离了困境。
“太感谢你了,林。”莎拉的声音依旧甜美,递过来一张纯白色的名片,边缘镶嵌着细小的银色暗纹,上面只有一行激光蚀刻的电话号码和一个抽象的雪花图案,没有任何头衔或地址。
“在莫斯科,也许你需要一个向导。”她的蓝眼睛注视着他,那空洞的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极其短暂地闪烁了一下,快得像幻觉。
林梓明接过名片,指尖触碰到那冰冷的纸张和凸起的纹路。寒意顺着指尖蔓延上来。他点点头,没有多言,看着她坐进那辆一尘不染的跑车,发动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