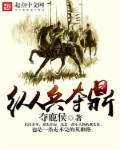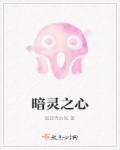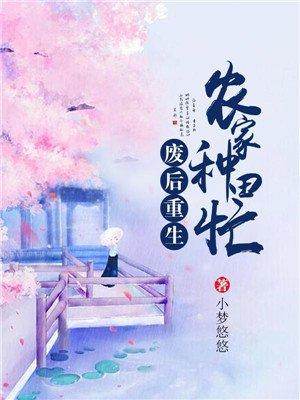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这世界危在旦夕为什么被禁 > 第五十七章 菜鸟(第1页)
第五十七章 菜鸟(第1页)
“南满铁路”的鞍山站很简陋,就是铁路线边一栋孤零零的砖石房子,是俄国人修“中东铁路”时建造的。
三角形的屋顶避免积雪堆压,立柱门廊下供乘客候车。四根黑烟囱在冬天冒着白烟,显得有些暖意。
日俄战争后,日本人给“南满铁路”修改铁轨,并将复线从旅顺修到鞍山站北面的“苏家屯站”。
国防军强势出关,赶走了“南满铁道会所”的日本人,收复沈阳周边几个站点的控制权,包括鞍山站。
日军间谍对沿线站点仔细侦查,确定在鞍山站东南和西南两侧各有一个国防军步兵营驻守,阵地上拉起铁丝网,用沙包和壕沟构建起环形工事。
当日军准备冒险,必须快速突破鞍山站,抢占“苏家屯站”,否则运兵效率太低,无法对沈阳造成足够压力。
12月7日夜,风雪甚大。
大岛义昌大将认为中国军队新兵众多,纪律不整,必然疏于防备。他下令两辆列车运载“南满铁路第二警备队”发动突袭,夺取鞍山站。
由于中日关系紧张,日本间谍没能靠近阵地具体侦查,但大概知道国防军的步兵营在阵地上布置了机枪和火炮。
为对付这种坚固阵地,日本“关东都督府”将六门150毫米口径的三八式重炮支援到一线给充当先锋的“第二警备队”充当“敲门砖”。
虽然在“南京事件”中,日本的“侨民义勇队”使用同款重炮并未发挥太大作用。但这是目前日军唯一能拿出手的野战重炮,别无选择。
旅顺重炮团的河本大佐亲自前来指挥自己的宝贝。当运兵的火车停在距离鞍山站七八公里外,他在黑夜中下令炮兵将六门重炮和挽马运下车。
中国军队把铁轨给拆了,火车没法直接冲进“鞍山站”。同样为运兵需求,日军火车要退回去,不能停留在原地。
夜太黑,风太大,铁路线旁的高粱地里乌沉沉的。收割过的田地里散落的秸秆和枯叶被吹的到处乱飞。
几片叶子吹到河本大佐的脸上,割面生疼,让这位日俄战争的老兵非常烦躁。为了照明,临时下车的地点亮着电石灯。这在黑夜中就是明亮的标识。
此外夜里气温太冷,穿棉大衣的日本兵都觉着手指头要冻僵。拖曳火炮的挽马发出嘶鸣,不愿从车厢上下来,拖延了不少行动时间。
“只要那些中国人有点脑子,我们此刻就暴露了。”
河本大佐不太认同大岛义昌大将的观点。他认为“南京事件”表明中国军队跟前朝的“鱼腩”不一样,已经拥有主动攻击的能力和意愿。
中国国内舆情民意正空前高涨,不可能在东北退缩。
但整个“关东都督府”的陆军部却不这么想。大批军官还带着五年前日俄战争时期的想法,觉着中国军队只会避战,不可能跟强大的日本皇军正面对抗。
这种刻板观念同样影响河本大佐的判断,他会下意识的认为在南京战斗的国防军跟在东北的国防军不一样。
废了半天劲,两吨多重的“明治三八式重炮”才从火车上搬下来。每门炮配套的六匹挽马也套上炮车,拉动前进。
复线的两列火车在哐当哐当的倒退,返回本次作战的出发地海州,去运来更多的日军。眼下在鞍山站外围只有“第二警备队”的八百多兵力。
铁轨被拆掉了一公里,短时间内是没法修复的。指挥作战的日军中佐硬着头皮,命令三个中队沿着路基展开散兵线,向北突击。
走了不到一公里,凌厉北风中响起枪声,紧跟着天空亮起一道强光,映照出地面密密麻麻的日军士兵。
日本警备队的士兵还在用老式的“金钩”步枪,上了刺刀,背着行囊。天空亮光后,不等小队分队的军官下令,他们训练有素的趴下,枪口警惕的瞄准铁路周围。
照明弹的枪声是北面来的,但不清楚具体方位。黑夜中也看不见中国军队在什么地方,但能明显感觉到对方的存在。
日军战略糟糕,基层战术搞的还是不错的。
士兵每月训练弹药不低于十发,机枪手不低于三十发。哪怕是铁道守备队,步枪手每年打掉的子弹也有个百把来发。
看起来似乎不多,但跟果党一年打不了十发相比就算“财大气粗”了。
在日军对面,国防军连长蒋翊武正急的冒冷汗。
两小时前,师部直属的装甲侦查营巡逻队发现了沿着铁路来袭的敌人。情况迅速上报,一直到沈阳城内的师部。
上级下令蒋翊武带队出击,迟滞敌军前进,摸清其兵力火力。
简单讲,别让日本人来的太痛快,给对方找点麻烦。就这么个简单任务,蒋翊武发现自己手下百十号弟兄完成的一团糟。
国防军第一师从全国抽调革命青年参军,工人学生以及各地新军都有。蒋翊武的队伍来自湖北新军。倒霉就在他有革命思想,但没受过军事训练。
黑夜中出击,也就刚刚完成新兵训练的步兵连跑啊跑的就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