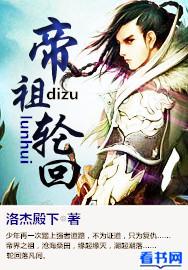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魔术师称nba仅4人影响全球 > 第十七章 斯德哥尔摩一九四九年(第4页)
第十七章 斯德哥尔摩一九四九年(第4页)
托马斯把信压在床边桌上的一本书下。过后他会再读一遍,然后把它毁掉。如果卡提娅和埃丽卡发现有过来信,问他内容,他会说没有收到。
在苏黎世机场,他们与米夏埃尔见了面,他朝父亲挤出一个笑容,然后拥抱了母亲和姐姐。他们朝车走去时,发现莫妮卡一直站在暗处。她没理埃丽卡和母亲,径直走到父亲面前,含泪拥抱了他。
“这不是哭的时候,莫妮卡。”她的母亲说。
“何时是哭的时候?”莫妮卡问,“又是谁决定的?”
“我决定的。”埃丽卡说。
当晚在酒店,埃丽卡和米夏埃尔拿出为托马斯收集的德国剪报,内容都是关于他即将进行的访问和可能去东德的行程。大部分持嘲讽的态度。托马斯尤其不解的是,有些文章批评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艰难时期留在德国。
“我若是留在德国就没命了。”他说。
片刻后,卡提娅来了,一脸坚忍和认命,然后眼泪汪汪的莫妮卡也来了。
“好了,莫妮卡,”卡提娅说,“我说过别哭了。”
卡提娅宣布说,每个人都得振作精神,因为乔治斯·莫奇曼要来了。托马斯曾在战前与莫奇曼会过一面,当时他在他的富豪父亲的要求下,来帮卡提娅的父母去瑞士避难。她的父母离开德国后,他与卡提娅时有书信往来,他一直表明,只要曼家决定定居瑞士,他一定会照顾他们。
“他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人,”卡提娅说,“我的父母很欣赏他。”
乔治斯一来,气氛就变了。服务员变得勤快起来,酒店经理亲自来到桌边,询问他们是否一切满意。
乔治斯·莫奇曼个子很高,衣着讲究,年约三十出头。托马斯想,是否可用精美来形容他,他就像一件高贵、精雕细琢的银器。但乔治斯一开口就不显得那么精美了,他的声音低沉,透着权威感和阳刚气。乔治斯的举止仪态显示他出身富贵,但他散发出一种托马斯几乎忘却了的东西。这种东西埃德加·冯·于克斯屈尔身上也有稍许,但那是断断续续的,而在莫奇曼身上,它闪烁着光芒。托马斯一眼看出,莫奇曼是那种与书、画、音乐为伴的人,正如他习惯于被用人侍候,让别人给他做饭。他视人有亲疏,带着一丝傲慢。托马斯发现,就连他注视餐桌和喝茶的样子,也来自瑞士富豪数代相传的慢节奏生活。托马斯注意到莫妮卡对这个年轻人敬仰有加时,差点笑出声。接着他瞅了一眼卡提娅和埃丽卡,她们都目不转睛看着乔治斯·莫奇曼。
乔治斯看到桌上的剪报,他翻阅了一下,耸了耸肩。
“我们不必理会这些,”他说,“德国人的恶意是无法消除的。”
接着他说自己并非是来拜访故人,而是来帮忙的。
“你们在德国和东区将会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抵达,如何离开。你们不能在火车站逗留。在东区,你们不能被人瞧见坐在政府的车里。我的别克车至少在瑞士的道路上畅行无阻,它也许是最好的旅行方式,我也可以当你们的司机。有必要的话,我准备穿上制服。”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看。”卡提娅说。
托马斯发现她在公开调戏这个年轻人。
事情安排好了。他会载着托马斯和卡提娅去埃格兰泰恩的瓦尔佩罗,让他们休息一下,然后他会接他们去法兰克福、慕尼黑,然后如果他们决定了的话,就去魏玛。埃丽卡将去阿姆斯特丹,莫妮卡回意大利,米夏埃尔继续随乐队巡演。
当莫奇曼驾车到瓦尔佩罗的施韦策霍夫酒店时,托马斯差点开口请他同住一天。他想商量一下访德的事。
“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待遇。我都不知道我为何要去。”
“你该明白,你无论怎样都成不了赢家,”莫奇曼说,“你待在加利福尼亚,他们会恨你。但你回去,他们还是会恨你,因为你一开始去了加利福尼亚。你只去西区的城市,他们会称你为美国走狗。但如果你去东区,他们会称你为敌方阵营的同情者。而且每个人都想要你去参观某个神祠、某座监狱、某个发生过暴行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觉得高兴,除了你自己,而你高兴仅仅是因为你将能很快返回加利福尼亚。战争是结束了,但它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人们心里有许多恨,在你访问期间,这些恨会指向你。”
一到酒店,乔治斯悄悄地叫来了经理。托马斯看到他把一大张钞票塞给了脚夫班头。他把经理介绍给托马斯后,小声说了几句,就准备离开了。
“你的名字不在登记簿上。你们的房间登记在我名下。不能让人找到你们。会有人来找你,很可能是记者。但他不会在这家酒店找到你。”
他们坐电梯上楼时,托马斯想,如果卡提娅说她累了,要独自用晚餐,他一点也不意外。但他们朝她房间走去时,她停下脚步说,希望能一起用餐,就他们俩。
他在房间的阳台上望着山谷的景色时,想到克劳斯会对此感兴趣,这是他父亲首次返德之旅。如果每晚能在酒店与卡提娅、克劳斯一起喝一杯就好了,克劳斯会评点那些发言、那些官员和群众的声音。一分为二的新德国是一个实验,它可以成为克劳斯写书的题材。
他想,在某些方面,他已经老得无法接受改变了。他想待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已经在构思一部可能会写的小说,他希望能活到写完它的那天。他想,他已经在一生中见证了足够多的德国。没有他,没有他的儿子,这个新德国也会发展下去。
晚餐时,卡提娅提起乔治斯出生于俄国,他的俄语讲得和德语、法语、英语一样好。
“这个家庭理应拥有财富。”
“我不知道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
“最初是因为做皮毛生意,”她说,“所以他们以前住在俄国。乔治斯曾有一次对我母亲说,现在他们以钱生钱。他的父亲与许多瑞士人一样,在战争中也过得很好。”
一星期后,托马斯和卡提娅坐卧铺车从苏黎世去法兰克福,而莫奇曼载着他们的行李开车过去。
由于德国报纸收到了威胁信,瑞士警察来他们的车厢护送,这让他们引人瞩目。到了法兰克福,他们被警察飞快地送到克龙贝格的政府招待所里。一路上他们看到楼房之间满地残骸。整条整条的街道似乎都消失了。天空是死气沉沉的泥灰色,仿佛也被轰炸过,失去了一切色彩。他们开车经过的街区被夷为平地,原来是商业大楼的地方只剩下水坑和干巴巴的泥土。就连走在破路上的身影也显得孤独而悲惨。
当他们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看到被毁掉一半的楼房时,托马斯抓住了卡提娅的手。这幕景象不知怎的比彻底的毁坏更直接,更有冲击力。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窗子掉了,屋顶也塌落了,这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曾经发生了什么。他端详着一栋楼房,它的整个外立面被轰炸掉了,每间房间的地板都一目了然,仿佛要举行一场多场景的话剧。他看到底楼的墙壁上还有取暖器,仿佛是在戏仿它们战前的角色。
莫奇曼来了之后,大家决定告诉所有已经到场的记者,托马斯在明日之前不接受采访。
当日傍晚在大接待厅里,他走来走去恍如身在梦中。人们问他是否记得许久之前他们曾参加过他的朗读会、晚宴、记者会。他只是报之以微笑,并让卡提娅跟在他身边。他数次问莫奇曼,他联系过的恩斯特·贝尔特拉姆有没有来。在此刻之前,他并不想见恩斯特·贝尔特拉姆,但在这个闹哄哄的地方,当男男女女都过来触碰他,争取他的注意力时,他愿意看到贝尔特拉姆朝他走来。
早晨,当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每个问题都聚焦在他是否会访问苏联控制下的东区。他说他尚未决定,但无人对此答案感到满意。当问到最后一个问题时,人群后方响起一个声音,问他既然大局已定,是否打算永久回到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