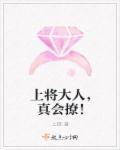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有一个聚宝盆动态漫画在线观看 > 第188章 女皇养成计划(第2页)
第188章 女皇养成计划(第2页)
马士英也是一脸的唏嘘,话说老马也没想到,苏州耆老会居然真爽快答应了,他把杨丰的税册五百里加急送到苏州,由新任应天巡抚郭维经转交给苏州耆老会后,第二天耆老们就匆忙开会,经过一番据说很激烈的商议后答应了。
毕竟也没前途。
他们直接关了玄妙观的门搞闭门会议。
杨丰说道。
“然后呢,他们就敢反抗了?”
更何况杨丰也没人可以去真的收税。
什么民?
我大清铁杆庄稼才是国人。
毕竟对于皇帝陛下来说,也就是老王在身边,还能让他找到点曾经那君临天下的感觉,而且老王也是主要替他和李自成打交道的……
他们只是在拖延时日而已。”
但绝大多数跟随西行的宫女太监都已经散伙。
但商议过程外面不知道。
宫女可以出去找个男人嫁了,太监也可以找个李自成部下将领当奴婢,反正伺候谁不是伺候,跟着崇祯连饭都不一定吃饱。
“只是此辈终究心怀不满,只不过想拖着而已,如今团练兵力不足,也多是乌合之众,堪用者不足两万,单以苏州算,无非那几千人,他们也知道以此不足以对抗朝廷。但此辈银子不缺,兵源不缺,大炮更易得,只需要拖个两三年,恐怕就有胆量对抗朝廷,那时候改革继续推行,各地士绅心渐齐,终究还是不能继续忍下去。
这个要求当然没问题,本来杨丰真正要的就是这个。
“一群守财奴而已,若非逼到走投无路,谁会站出来拼命?
银子而已,他们就不缺银子,一年多拿两三百万而已,单单扬州那群盐商们,一年利润不下九百万,苏州半城的织机,苏州城外无数织机,单单一个盛泽镇都能喊出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他们可比扬州盐商有钱。
当年一个徐家就田四十万亩,织工数千,算起来一年百万两可得,而江南如徐家者何止数十。
都是锦衣玉食的,谁会为这点银子拼命?
再说这银子真没了?
以那两百八十万石为例,他们真得去别处买粮?谁家不是满仓的粮,他们交税折银,可收租不是折银,太湖这一圈皆良田,一亩地三四石谷是少的,六七石者不足为奇,地租就找不出几个低于一石半的。朝廷税才收几个,一亩地三两斗而已,还得是重赋官田,这些士绅收的五倍于朝廷,两百八十万石不过百万亩的租子而已,哪里还用得着出去买粮。
只是不能以二两一石卖出,才觉着自己亏了。
那不是往外掏银子。
而是要少赚银子。
少赚对他们来说就是亏了。”
马士英说道。
他对江南士绅还是了解的。
就这些一辈子锦衣玉食,在园子里逍遥快活的家伙,还能有造反的勇气那真就是见鬼了,要说士绅里面有些硬骨头这个的确是必然,但耆老会是耆老们会议决定,指望一堆各怀鬼胎的耆老会齐心协力,准备冒着灭门的危险起来造反,那就更见鬼了。
跪下不好吗?
杨丰要的再多,对他们来说也都只是些唾手可得的东西而已。
但性命,家族,没了那就真没了。
“那百姓为何饿到造反?为何都说朝廷苛捐杂税?”
公主好奇地说道。
杨丰几个都微微一笑。
“公主,百姓交赋税的确就是一亩地两三斗,而且还是苏州这些重赋官田才这么多,这些田是官田,民田以太祖规矩都是二十税一,三十税一,只是苏州一带特别,多数都是重赋官田。这个也没办法,江南水田一亩地多的都能到七石,平常的也是四五石,可北方上上田才两石,平常的不到一石,尤其是西北辽东,山区这些四五斗都算好的。太祖高皇帝英明,在这亩产高的地方多收些粮亩产少的少收些,亩产四石的地方收四斗,还能剩下三石六,亩产四斗的地方,就是收四升也只是剩下不到人家零头。
取有余而补不足。
治国就得如此。
毕竟这天下大了,膏腴之地的是大明子民,贫瘠之地的也是大明子民,为君终究得兼顾南北。
可如今的大明,早就不是太祖时候了。
天下之田多半早已入士绅之手,种田者无非佃户,甚至僮仆,此辈血汗所出之粮,大半要给士绅,后者那些重金所建之园子,养的姬妾,家里多至数千的奴婢,子孙锦衣玉食,都是要从这些粮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