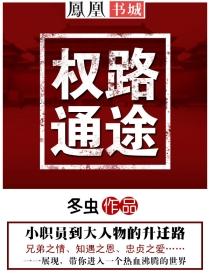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睚呲必报太子妃 > 十九(第2页)
十九(第2页)
待瞧不见青音的影子了,严鹊娘方才出声,使唤下人道:“切莫拿去洗,将六姐儿用过的茶具都好生收起来,送到我屋里去搁着。”
她脸上充斥着阴森而不正当的诡异感,炯炯有神的双目却又泛滥出少女春意。
那便是狂人的友爱。
回了院子,巧鞠搀扶着姐儿坐下,终是忍不住道:“百闻不如一见。五少奶奶同奴才们背地里嚼舌根子说的倒一点不差,有些神神叨叨,是个疯疯癫癫的。”
巧鞠嘴毒,青音也不诘难她。
珍珍呈了茶盘上来。
青音倦了,瞄一眼,手指在左下角那格上敲了敲。水已煮沸了,珍珍立即去洗了茶叶泡上来。
“疯疯癫癫的。脑子却很好使。”青音道。
大严家的女流之辈,少年之身,从前力挽狂澜使得严家收入翻番的。嫁出来当真是可惜了。不过严鹊娘自个儿似是从未觉察过她究竟有多天资聪颖。就这么一头扎进了极其苦的爱恨热潮里。
到底多情善感是女子。
再说了。
狂人,她又何尝不是呢。
青音望向自己手中那瓶小巧玲珑的毒。
-
后来岑滞云与姒违尚见过一面。
是受降时。魁梧的蛮族将领右手包扎,见岑滞云时匪气十足地笑了声:“托你和你妹子的福,险些再也拿不动刀。”
岑滞云笑:“那岂非美事一桩。免得大人再杀生了。”
姒违怎听不出他话里挖苦。
交战间,互相都杀了彼此成千上万人。要追究,也是血海深仇,但武将之苦,又教人惺惺相惜,就此别过便是至善至美了。
于战场上岑滞云已然是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军之子了。然他年纪这样轻,全京城贵女们无一不是虎视眈眈的。光是他凯旋那一日,寻常百姓家倾巢出动不提,就连官僚贵族家,也几近是一一遣人来岑府道贺的。若非家主谢客,只怕岑府的门槛都要踏破了。
岑威道,古有仲永泯然众人。舞刀弄枪、动众行军之事,滞云贤于材人远矣。他不希望岑滞云耽于饮食声色。
自然,也不过是冠冕堂皇之辞罢了。
继子的风头盖过老子,那还了得。
退一万步说,方才进岑府时,滞云早不知杀过多少人、见过多少皮开肉绽血流成河的光景。
他是刺客头子,拿刀抹人脖子时眼睛都不多眨一下,旁人流血多,自个儿流过的血更多。只不过活到最后、笑到最后的总是他,仅此而已罢了。
公子说,你是杀不了岑威的。
光阴似箭,头一回听见这话,乃是天命在江南那艘船上刺杀告败时。岑威不愧是号称上下五百年唯一配得上大将军之名的武将,轻而易举,不过两三下便稳定军心,做了拉长战线的部署,当即将人数处劣势的刺客推入消耗中。
不得已唯有拆开锦囊。公子已料到岑威的下一步、乃至于下下步棋。
他命滞云去假扮岑家的继子。
并非为的伺机而动刺杀岑威,来日方长。从军事上来说,借岑威之子这个头衔所能取到的东西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