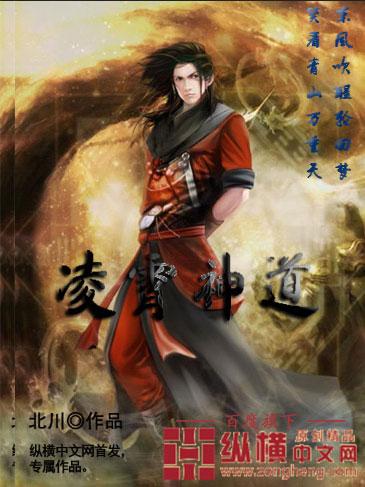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再婚女人演员介绍 > 第四章 人生是没有退路的单行线(第9页)
第四章 人生是没有退路的单行线(第9页)
景萱和阿弥姐相互对望一眼,景萱问:“怎么个情况?听你这意思,不会是和我哥又生事端了吧?”
江若禅叹气:“他铁了心,要和我离婚。我这都半个月没见他的人影了。”
“啊,还动真格的了?肯定是你又惹他了吧?”
江若禅把那些天发生的事叙述一遍,悲叹道:“我也不知道是啥命,事事拧巴。嫁了个帅哥吧,人家傍富婆去了。又嫁个有钱人吧,年龄大不说,儿子闺女扯不完的麻烦事。不喜欢的人,天天缠着腻着打都打不走;喜欢的人吧,又自私又胆小,只想着自己。烦死人!”
阿弥姐将信将疑:“不会吧?展宽这定力这么好?怎么能面对美女不动凡心?”
景萱也不明白:“真是让人看不透。他不会是有难言之隐吧?”
景萱和阿弥姐再次对望,同时开口:“难道是……”
俩人心照不宣,爆笑起来。段越站在旁边,也忍不住乐。
江若禅也憋不住笑了,手指一一点过去:“咳,我说你们就不能心理阳光一点?就没想着人家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坐怀不乱的真君子?”
“不可能。”那两个人又异口同声。“你这样的美色当前,哪个男人能不动心,真是奇了怪了。”
“他明明是喜欢你的,傻子都看得出来。”
江若禅忽然烦躁起来,把手一挥:“算了,不提他了。他又不帅,又不年轻,又自私,我怎么就偏偏喜欢上他呢?真是贱啊。”
“谁喜欢谁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些时候也不因为他是否帅或者有钱。可能都是命中注定的吧。”景萱说。
“可不,那个邹家诚不也迷若禅迷得颠三倒四的。”
“咳,归根结底,还是我身边优秀的男人太少了,没有让我崇拜的人。男人吧,要么帅,要么有才,要么有财,我喜欢优秀的可供我仰望的男人。认识的人中,还就展宽还差不多,有点才,有点财,但也都不咋样,缺乏激情。总之啊,我就是命苦……”
“你这还命苦,好车开着,别墅住着,锦衣玉食,粉丝大把,今天这个请喝茶,明天那个请唱歌,生活多丰富多彩啊。你这算命苦,我们还活不活了?知足吧你!”景萱愤愤不平。
江若禅白了她一眼:“亏你还是作家,看问题光看表面。就不能挖掘一下浮华背后的真相?”
阿弥姐担忧地说:“若禅,你真的打定主意要离婚?你也真是糊涂,怎么能那样逼他呢?”
“我那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嘛。谁知道就把他惹急了。”
“你别糊涂了,还是展宽说得对,等他回来,你好好认个错。你们俩也是10年的夫妻了,他不会不知道你的为人。”
正说呢,江若禅电话响了。她接起一听,立刻脸色煞白。
电话是张华成的司机小余打来的:“禅姐,张总他,他刚才在工地上,被一根钢板砸了腿……”
江若禅“呼”地站起来,她的声音都变了调,对着电话吼:“他现在怎么样,送医院没?你们赶紧叫救护车啊!”
“我们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哪家医院?我马上到。”
“J城第一人民医院。”
江若禅收了线,心急火燎地拿包出门,交待他们:“张华成在工地受伤了,我得赶紧去医院。段越,下午你帮我去接一下果果,我回来之前果果就暂时交给你们。”
景萱应着:“放心吧,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江若禅早已旋风般地出了门。
留下三个人面面相觑,人生真是福祸无常啊。
江若禅驾车上高速,一路疾驰,直奔J城。
三个小时后,她在J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导医台急切地问询:“请问骨科在几楼?”
“三楼,左转。”
江若禅风风火火地找到张华成的病房,到了门口,她反而不敢进去了。她扒着门缝,看到他打着石膏高高吊起的左腿,和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的头,她无力地靠在门框上,泪水无声地涌满了眼眶。此刻,她心里充满了懊悔。如果不是自己没事找事逼他分财产,他也不会愤而出走,更不会在工地上呆那么长时间不肯回家,自然也不会引发这一场祸事。
她该怎样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啊?
司机小余从里面出来,看到她,惊叫:“禅姐,你这么快就到了?怎么不进去?”
江若禅赶紧擦擦泪,问:“他怎么样?”
“左腿粉碎性骨折,刚做完手术,头部也受了轻伤,但医生说问题不大。”
江若禅担忧地望望里面,问:“到底怎么回事啊?让你跟着他照顾他,怎么还出这么大乱子?”
“我也搞不明白,以前张总出差都是到工地转转,看看工程进度,安排一下工作,就回来了。这次他好像打算长住那儿了,每天亲自去监工。这不,今天他在工地转悠,吊车出了毛病,一块钢板砸下来,一下就把他压在下面了。幸好钢板的一头担在一堆木料上,否则,后果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