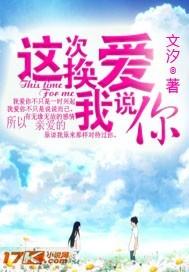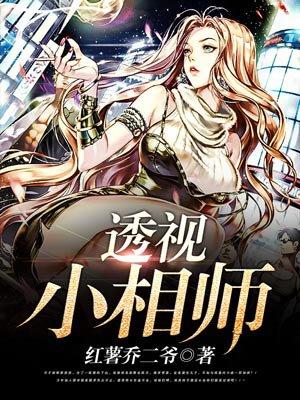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鬼谷神谋 > 第六百七十章有为无为(第2页)
第六百七十章有为无为(第2页)
道若用言来表,也就有了其外形,可以用心感受。
如同这万物,如同这时节之变换一样,这都是道现,有形之物,却含无形之道。
从有明无,也就是师傅所言有欲而观道。”
“不错,禅儿所言正是道之两面,师傅之所以不想言,就是因为言而非道,妙不可言。
只是世间众生却又喜欢道学,追逐道之真谛,却又不得共法门。
而明道亦可与道存,与道相通,若世间之人皆能明道,就会依道而行,可这也只是理想之态。
而师傅之所以不得不言,也只是我之所言,只是道现,而非真道,故心有惶恐。
日后我与你所传皆是如此,我所观之道,未必就是你所观之,可却并不影响道之存在,你若欲明道,自当用本心观之。
师傅只是引路之人,而非道之本身。”
老子十分温和,也十分谦虚,对道始终保持着敬畏,保持着一种敬重,纵然是自己对道之所明已超凡脱圣,可一说起道还是十分卑下。
而且此时所言,也是对王禅十分高看,像是有遇知己一样,王禅能领悟他的道法,也是对他的认可。
而且老子传道,并不像其它人一样传教的东西,就必须让徒弟依自己所为,认为自己的所说所行是对的。
而老子只是传之以法门,至于王禅所能明什么道,却在于王禅,而非老子传教之人。
“徒弟谢过师傅,若不是有师傅明道之法门,徒儿也会与常人一样误入歧途,最后不仅不能明道,甚至会陷入无尽的迷茫之中,在道的万千世界之中受困于万千世界。”
“好好好,既然如此,那今日师傅再传你一些体会,权作与你自己思虑的引导。
天下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美的东西与事物,是因为有对这个事物一个评判的标准,就如同对美好的东西一样,如有人之美丑,人之善恶,有了美与善的标准。
那么也就会有了相反一面的标准,知道美与善,也就知道恶与不善是一个什么样子。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有生于无,无生于有,如果不是看到现在的万千世界之有,也不会想到道之本无,有极而无。
难相对于易生,相辅相成,难成之事,自然与容易之事相对,若无容易之事,世间也无难事,去此而失彼。
长与短相形成较,长相对于短而言才称之为长,短相对于长,才成其短。
可世间却也无绝长之长,绝长若短,都是相生的。
世间也无绝短之短,绝短若长,与大小之理一样,万千世界之大,大极至无。
高与下相对成映,无高自无低,就好像声与音相成,前与后相随一样,身前与身后,自以己为度,世间之物,相对而言,相对而成,这是一件永恒不变之事,就像阴与阳一样。
有阴才有阳,阴阳化一,一化无,有若男女,有若天地,有若水火。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说完,看着王禅,而王禅则也是微微一笑道:“师傅高论,实让徒弟见识非浅。”
“禅儿,前面物物相对之说,本是这世间长存之理,你已习易理多年,自然容易明白,可后面这些,为何你却不问,世间之人总是会因此而误会,还以为我老子教人,是误人子弟,让人无所作为,你若明白,你来说与师傅听听。”
老子知道若论及阴阳,相生关系,这一点考不到王禅,普通聪慧之人也能有一听就懂,可后面的就十分生涩了,普通人难与领会其中之意,就算是聪慧之人,也难解,更会误解老子的意思。
(要正确理解这段道德经,其实要与上一章节里的关于道的定义及论述相关联才能得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