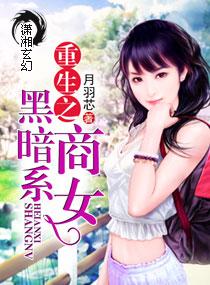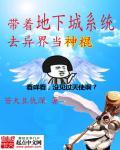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边境插队手记 > 第173章(第1页)
第173章(第1页)
十分感谢一年来始终关注《边境插队手记》的博友,假如不是你们的鼓励,我会觉得无趣而半途辍笔的。其间包括一些博友一直在帮我纠正文中的错别字,以至于这篇《边境插队手记》尽管文笔平庸,但差错率却相当的低。
这,足以让我欣慰了。
作为知青运动的结尾,我想有个大背景还是应该了解一下的:插队知青的&ldo;病退&rdo;,只不过是全体知青大返城潮流的前奏,在前奏与大潮之间有这样一个导火索。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ldo;试行草案&rdo;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知青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于是以云南知青请愿方式开始、以黑龙江&ldo;今夜有暴风雪&rdo;方式结束的全国知青大返城,就如黑龙江上淌冰排那样汹涌澎湃,冰裂、断层、挤推、撞击……就像当年这些学生从城里集体消失一样,短短的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知青的千军万马也从农村忽拉一下消失了。
这个与&ldo;文革&rdo;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都相应延迟了两年多的上山下乡&ldo;一片红&rdo;,终于成为历史。
从此以后,共和国不再会有中学毕业生集体全部下乡的极端;恰恰相反,在知青的返城潮过后,是规模更大的数千万农民的进城打工潮。
即使那些至今还&ldo;无悔&rdo;并高唱着&ldo;知青精神万岁&rdo;的过来人,想必也不会逆潮流而动,让他们的子孙去重蹈覆辙了。
熟悉我的朋友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文中的某某是谁呀?
我只能这样回答:作为纪实性小说,文中大部分人已经被我拆分和重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谁是谁了,但当年农村的细节却是真实的并保持着新鲜的气味。
我在文中只对个别人保持了原样的记录,其中的&ldo;汪永德&rdo;就是。
他的真名叫江财妙,他回上海搞病退后,我在哈尔滨上大学,一直没见过他。
一晃几年,有一次回上海探假,我向知青打听。知青告诉我:他得胃癌死了。
在悲哀的伤痛中,让我唏嘘不已的是:曾经的&ldo;浪子&rdo;江财妙,返城顶替父亲进了公交公司当售票员,道地的东北普通话,加上热情的服务,还有对公交车上小偷的敢于斗争,使他获得过上海市公交系统的劳动模范,他真的做到&ldo;回头金不换&rdo;了。
剩下活着的,我只能从心里祝福而不愿意再惊动他们,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知青都愿意回头去捡拾那段生活的。
曾经的插队战友,只有少数后来当官、当教授、经商,成了现在社会上一部分活跃的人群;大部分却沉淀在社会的最底层,日子过得并不理想。这是个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目标、到后来又各自分飞的群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境插队手记》也只是个人的经历,并无代表意义,唯一的价值就在它是纪实的。
作为这段&ldo;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do;的亲历者,我有幸保存了当年的手记,扔了可惜,故缀成一册,供现在喜欢的人闲时一阅,也供将来的研究者作为参考。
为了《边境插队手记》的完整,我还想作一些如下的后记:
记得我初考完从县城返回生产队那天,副队长老吴和我一起蹲在地头,他说:&ldo;听到了小麦拔节的声音。&rdo;
我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天,静静地,啥声也没有呀?
他笑笑,抽着大旱烟,不再言语。
就像一个谜,闲时我就想:老吴听到的小麦拔节声到底是咋样的?
好多好多年以后,我重回爱辉,忍不住问老吴。
此时已经一头白发的老吴哈哈大笑:那不是说你要上大学么!
哈哈哈!我也大笑,谜底竟是如此简单。
可不是么,家里老户口本的附页上,对我的仅有记载是这样的:
1970318,黑龙江爱辉县插队,盖着&ldo;迁出&rdo;章。
1982719,黑龙江大学分配,盖着&ldo;迁入&rdo;章。
无情的记载,遮不住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上海,把一个实际上只有小学六年级学历的我送去了黑龙江;黑龙江,却把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还给了上海。
我并不怀念那个年代,但我要感谢黑土地,那里,曾响起我生命的拔节声!
我还记得,离家13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上海。
父亲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我,说:&ldo;完璧归赵吧。&rdo;
&ldo;这是什么?&rdo;
&ldo;你写的信呀。&rdo;
我简直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所有我写的家信都按年月顺序排着。
一种甜甜的滋味涌上心头,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家信会再回到我的手中。这些信带着弟妹们的朗读声、父母亲的舐犊情,它们随同我在农村16本大大小小的日记一起被珍藏了下来。
包括后来一位转点走的知青,也在三十多年后把我写给她的信还给了我。
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记忆如此好,能把当年的情景像画面一样记录下来?其实,如果没有那些偏重于故事的日记、父母替我保存的家信、知青战友归还我的书信,我又哪里能记得住这么多细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