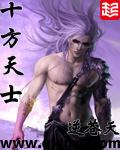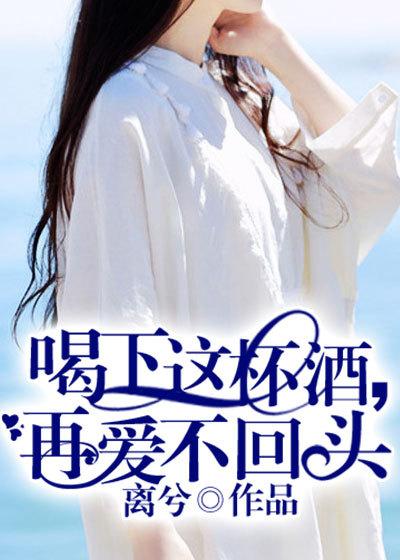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三国征服者 > 第154章(第1页)
第154章(第1页)
整辆座车华贵中透着威武,尤其是今天刘宏还特地穿上了全副铠甲,看上去更是威风凛凛,颇有一副大将军出征的气势。皇帝的座车再往后就是由射声校尉和司马吏士乘坐的随从车,也一律是轻车,上载矛戟等兵器,配有五色旗,最后一辆则悬挂豹尾。
皇帝出行自然是戒备森严,最贴近的当然是几位中常侍和小黄门,周围更有众多的羽林郎和虎贲护卫,另外,车队的两侧还各有大批的羽林骑兵护卫着,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斩杀任何没有皇帝命令而胆敢靠近的活物。
看到皇帝的车队接近,众大臣以大将军和三公为首纷纷上前跪倒迎接,张扬自然也不敢怠慢,军中更是鼓号齐鸣,声震四野。
刘宏下车登上大坛,扫了一眼台下排得整整齐齐的庞大军列,满意地点了点头,心情是格外之好;转头对一旁的张扬笑道:“爱卿果然是治军有方!此次出征,朕看是定能凯歌高奏的了。”
身后尚书卢植听完,上前一步,躬身奏道:“恭喜陛下!有此良将精兵,定可扫平宵小,保我大汉基业。”张温等也纷纷出言附和。
一旁的何进听了眼中闪过一丝妒色,沉着脸在一旁默不作声;张让的眼睛飞快地一扫,将何进的神色收进眼底,脸上却满是笑意,一副很是赞同的样子。
张扬这时候上前回道:“为国出力,是臣的职责所在,请陛下放心。”
刘宏点了点头,道:“时辰不早了,开始吧。”
“是。”张扬向皇帝行了一个军礼,回身接过李晨手中的令旗一挥,坛下早已等候多时的号手忙一起扬起了手中的号角,就听“呜呜----”的一声长鸣,悠长威严的号声刹那间传遍了整个场地,紧接着就是一通滚雷般的战鼓声。
刘宏在张扬的引导下下了高坛,登上了一匹披上了胄甲的白色战马,开始一个一个方阵地检阅士卒。每到一处,众士卒都在带队的校尉或司马的一声喝令下或以矛戟拄地或以刀枪击盾,“硿硿硿”三击之后又是三声高呼--“万岁,万岁,万岁!”整齐划一的敲击声和呼喝声配合着战鼓声,震得地皮发颤,震得人心悸,胆子小点的怕是站也站不住。
刘宏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规模的阅兵,虽有张扬事先解释说明在先,又有骞硕亲自牵马护卫在侧,仍不由感到阵阵心摇神弛,面上隐隐便有了一丝不安之色。
不过等渐渐习惯了后,却又开始被这一山呼海啸般的壮观威武的场面刺激得兴奋了起来,到后来甚至挥退了骞硕,自己骑着白马在军阵中慢慢小跑了起来,让骞硕心中叫苦不叠,却又不敢不紧追在后。
绕阵三匝,刘宏终于有点意兴阑珊,满面红光地来到了小坛下,在赶上来的骞硕的帮助下翻身下马,登上高坛,面南背北而立,从小黄门手下接过印信兵符,兴奋的高声道:“张扬何在?”
张扬按捺住兴奋的心情,上前一步,单膝跪地,大声道:“臣上军校尉张扬等候接令。”
刘宏手捧印信兵符,大声道:“朕命你即刻领军出征,务必扫平逆贼,彰显我大汉之威。”
“遵旨!”张扬一边大声回应,一边双手高举过头,接过了兵符印信。
刘宏又伸手解下腰间配着的长剑,递过去道:“朕还赐你宝剑一把,你可凭此剑节制豫州诸郡大小官吏,并允许你先斩后奏,爱卿可莫要辜负朕的期望。”
张扬一听,心中又是惊喜又是兴奋,这不是代表自己在汝南就是老大了。
张扬将兵符印信交到左手,伸右手接过长剑,平举额上,高声道:“请陛下放心!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完,叩首再三,起身后退一步,反身面对着台下静静地等候着的大军,猛地将手中长剑高举过首,高呼:“必胜!”
台下众军见了,群情振奋,也一起将手中兵刃高高举起,齐呼:“必胜!必胜!必胜!”这一刻,当真是刀枪如林,呼声震天,直如群山崩塌,巨浪拍岸一般,连一直未曾停过的寒风也似乎被吓得安静了下来。
张扬满意地点了点头,收回长剑,大声道:“出发!”身后李晨手中令旗挥动,大军便按着规定的顺序依此出发,如滚滚洪流般踏上了征途。
☆、第九十三章路遇良才(今日五更冲击新书榜,在此求推荐,金钻)
从洛阳到汝南,大致上有三条路线可以走。一条是顺河水而下,经阴沟水、汤渠绕到项县,从东北面逼近汝南黄巾的老巢葛陂,这条可称为北线,因为一路上以水路居多,后勤运输方面方便不少,就是路程远些。
一条是向南出大谷关,到梁县,再顺汝水东下到郾县(今河南漯河市西),再往东就是汝南地界了,这条可称为南线,因为山路少,行军相对容易些,不过也要绕点路;再有就是向东南出轘辕关,翻过嵩高山(今河南嵩山)到阳城,然后顺颖水东下到郾县,这条可称为中线,路程最近,但到阳城这一段相当难走。
对张扬来说,他不光要打赢这一场平叛之战,还要尽可能迅速地结束战事,赶回京城。不知为什么,直觉上他总是对京城的形势有点不放心,尽管何进和张让方面最近显得非常平静,尽管他已经通过卢植的帮助以士林派推荐的方式将郑泰和华歆分别送上了御史和议郎的位置,使得他在朝中总算有了自己亲信,尽管他特地将杨安国留在了京城以保证随时可向他传递京城最新的动向,但他就是不能完全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