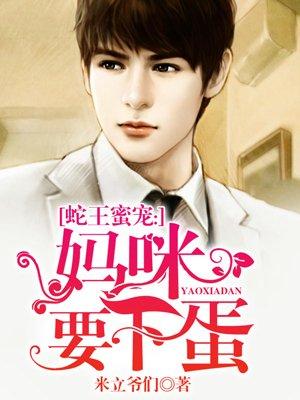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幻空梦记 > 第90章 空心论道(第6页)
第90章 空心论道(第6页)
“钱管家,主母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若是对面几个大人不嫌弃的话,可以让病者与她坐同一辆马车。”
钱管家支支吾吾道:
“可是这……男女授受不亲,有违礼法啊!”
那丫鬟道:“钱管家,主母说了,命者为大!”
钱管家还在那里支支吾吾道:“毕竟这颇为不妥当啊!,春菊,你再问一下主母意思吧。”
春菊便又回去,不一会过来直接对赵无贵讲道:
“我家主母请贵处大人与她暂乘一辆马车,等有车再换!”
赵无贵跑回去向董何夕禀告,董何夕听完之后道:
“这有违礼法啊。”
秋菊见赵无贵去了好久不见回来,忙跑过去,不想正好听到董何夕的话,秋菊道:
“你这大人,端的是愚昧,我家主母尚且不避,你又怕些什么?
况且人命为大,岂能为了些所谓的名誉,而枉顾人命呢?
还请大人快快上车,然后早日为大人寻找到合适的医师进行救治。”
董何夕看了看众人,无奈道:
“如今也只有此一个方法了,大宝,无贵,扶着我上马车。”
柴大宝和赵无贵慌忙上前将董何夕扶上马车。
在距离上马车前,董何夕又回头向秋菊问道:
“这位小姐,不知我该如何称呼你家主母?”
秋菊笑道:
“我可不是什么小姐,叫我秋菊就行,我家员外姓钱,您直接叫钱夫人即可。”
董何夕听完才上得马车,可是刚要上马车,又看向秋菊道:
“还请秋菊姑娘向钱夫人请示一下,这路旁的独轮车上的老夫人也有病在身,行动不便,可否一同乘坐马车,一来是钱夫人的一件善举,二来我等三人在车上,也好避嫌!”
秋菊却打趣道:
“你这大人怕不是主要是为了避嫌吧!”
此话一出,董何夕一脸通红,而马车的钱夫人道:
“秋菊不得无礼,快快按照大人的话,去扶那位老夫人一同前来乘坐马车!”
秋菊忙答道:“是!”
而董何夕向柴大宝道:“大宝,你也一同前去,免得搞出误会来!”
柴大宝道:“大人,你这身体!”
董何夕道:“无碍,且这里有无贵就行!”
于是柴大宝与秋菊一同前去,不一会狗剩儿推着狗剩儿他娘就过来,于是,狗剩儿与秋菊先扶着狗剩儿他娘上车,仔细去看,秋菊却一直扭着头,皱着眉头,董何夕看见秋菊的样子一声叹息,内心不禁对秋菊的评价低了几分,但是他也不好说些什么,只是心想:
“同是苦命人,如何如此嫌弃一个老人家!”
可是等他上了马车,一看钱夫人用手捂着鼻子,将头伸向车窗外,样貌未曾看清,而此时一阵酸臭之味道却弥漫于整个马车之内,顿时熏得他头晕目炫,此时他才明白刚才秋菊为何是那副表情,心道:
“我一个男子与这老夫人靠近,尚且受不了这味道,况且一个爱干净的小丫头呢?真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若非身临其境,难知其中艰辛啊。”
而柴大宝是何须精明之人,他一见秋菊的表现,心道:“以我观之,秋菊这丫头决然不是什么嫌贫爱富之辈,想是必然有什么缘故!”
等扶狗剩儿他娘上车之后,他马上上前悄声向秋菊问道:
“秋菊姐,刚才缘何扭头皱眉啊?”
秋菊小声道:
“这老夫人怕是许久没有洗澡,一身的酸臭味实在是……”
柴大宝昂了一声心想道:“你们这些人哪里知道我们这些穷苦之人的生活,有几个能洗澡用牙粉,这一辈子怕是只有出生洗去身上的胎水时,洗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