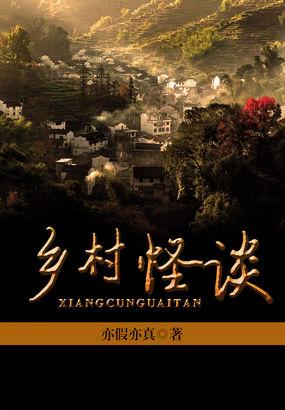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成了我男神的饭友 > 第165章 不止是相拥而眠(第1页)
第165章 不止是相拥而眠(第1页)
疫情期间的娱乐有风险,很有风险。
就比如玩完这次密室逃脱,我们很不幸地成为了时空伴随者,居家隔离了几天。
向来散惯了的姜昂突然被关在了家里,闲得浑身痒痒。
也不知道抽了哪门子疯,一天一个视频给我打过来,跟我炫耀他做了什么吃的。
切,跟谁没有似的。
核酸绿灯后,剩下的一个月,我们老老实实待在了家里。
九月开学,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校园。
只不过,这一次没有三个叽叽喳喳的女孩像嗷嗷待哺的雏燕一样等着我给她们分吃的了。
新室友人也不错,但不知为什么,我对她们始终亲近不起来。
也许是因为我每次给她们带我妈妈做的菜,她们的表情都很古怪吧。
读研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理论课上起来比本科的时候累多了,还要全天候着导师的消息。
不管我是在约会,还是在睡觉,只要导师一个电话,我就得爬起来。
理论上完,介入临床,按时轮科。
很累,很累。
是以,我每天的慰藉除了见到许星朗,就是能回到寝室好好睡一觉。
可是这一天,当我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我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气味。
我无奈地敲了敲我隔壁床的床杆,“你上完厕所能不能把马桶冲了,等着留到下顿吃吗?”
她叫史筱意,是个长着娃娃脸的女孩。
初见时,就数她对我最热情。
没想到后来,偷用我护肤品的是她,说我妈做的菜上不了台面的也是她,赶在我和我许星朗见面时非要凑过来的还是她。
不过没关系,这些我都可以忍。
但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她上厕所不冲,连用过的卫生巾都能放在床上,屡教不改,偏偏还住在我旁边。
我每天都被熏到翻白眼。
史筱意闻声从床帘里露个头,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嘴却硬气得很,“你凭什么说是我?我还说是你拉完不冲呢!”
又是这么的不讲理。
所以她的意思是,我人还在外面,就能隔空把这坨屎转移到我们寝室的马桶,来诬陷她,对吗?
……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我刚想跟她硬刚,一旁的董婷婷和黄芊便过来拉我,“好了好了…”
“都在一个屋住着,没必要闹这么难看。”
我:……
“没必要是吧,那你俩留在这天天给她冲马桶吧!”
这屋真是没法待了。
一个不爱洗澡的屎王,一个早起外放刷手机,一个白天疯玩却总在半夜躲在被窝翻书学习。
怎么奇葩全让我碰见了。
我拿起包就冲去了导员办公室。
今天要么她搬出去,要么我换寝室。
但导员给我的回复是,现在没有可调换的床位,让我再跟史筱意沟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