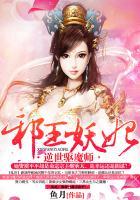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重案六组之暗影之下 > 第986章 旧巷里的回声(第1页)
第986章 旧巷里的回声(第1页)
青柳巷的路是青石板铺的,被经年累月的脚步磨得发亮。季洁踩着石板路往里走,鞋跟敲出笃笃的轻响,惊飞了墙头上几只啄食的麻雀。巷子不深,第八号门是座老式的四合院,朱漆大门早已斑驳,门环上的铜绿爬满了岁月的痕迹,门楣上"家和万事兴"的木匾,漆皮剥落得只剩模糊的轮廓。
这是李梅和林慧母亲生前住过的地方。根据李梅的供述,玉佩背面刻的地址就是这里。案子虽然基本理清,但季洁总觉得心里还有块没熨平的褶皱——李梅说母亲留下玉佩时曾言,凭着背面的信息能让失散的姐妹重逢,可她们明明一直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为何直到林慧遇害前,似乎都未曾真正相认?
她抬手叩了叩门环,铜环撞击木门发出沉闷的声响,在安静的巷子里荡开涟漪。片刻后,门内传来拖沓的脚步声,接着是个苍老的声音:“谁啊?”
门开了道缝,露出张布满皱纹的脸,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戴着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浑浊却带着审视。“你找哪家?”
“您好,我是市局的,想问问这里以前住的陈家的事。”季洁亮出证件,“就是陈秀兰阿姨家。”陈秀兰是李梅和林慧母亲的名字,档案里有记录。
老太太眯着眼看了看证件,又打量了季洁半晌,才把门缝开大些:“陈家啊……搬走好些年了。我是后来搬来的,住了也有十年了。”她侧身让季洁进门,“进来吧,站门口说。”
院子里种着棵石榴树,枝繁叶茂的,遮住了小半个天井。树下摆着张石桌,几个石凳东倒西歪地放着。老太太引着季洁在石凳上坐下,自己搬了个小马扎,慢悠悠地说:“我来的时候,这院子空了快一年。听街坊说,陈家大姐走得突然,俩闺女也不知去了哪儿,房子就这么搁着,后来房管所才重新分的户。”
“您知道陈阿姨的两个女儿吗?她们后来回过这里吗?”季洁从包里拿出李梅和林慧的照片——是从档案里翻拍的,像素不算清晰,但能看出轮廓。
老太太接过照片,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仔细端详了半天。“左边这个……看着有点眼熟。”她指着李梅的照片,“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就在门口站着,看了半天就走了,没进来。那时候我刚买完菜回来,瞅着她眼圈红红的。”
季洁心里一动:“大概是哪年的事?”
“记不清了,”老太太摇摇头,“许是三四年前?天挺冷的,她穿个黑棉袄。”
那正是林慧离婚后独自带着乐乐生活的日子,也是李梅被赌债缠上的开始。季洁追问:“那您见过右边这个吗?”她指着林慧的照片。
老太太又看了看,摇了摇头:“没印象。倒是听对门的张奶奶说过,陈家大姐走后第二年,有个年轻姑娘来打听,说找姐姐,张奶奶跟她说人早搬走了,那姑娘就哭着走了。”
季洁沉默了。看来姐妹俩并非从未寻找过彼此,只是命运总在她们之间设下错过的藩篱。李梅或许是碍于生活的狼狈,不敢上前相认;林慧或许是打听无门,只能把思念藏进那半块玉佩里。
“陈家大姐是个好人啊。”老太太忽然叹了口气,“我听老街坊说,她男人走得早,一个人拉扯俩闺女,在巷口摆了个修鞋摊,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容易。那俩丫头小时候总在这石榴树下玩,一个文静,一个皮实,老远就能听见她们笑。”
季洁的目光落在石榴树上,想象着两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围着树追逐的模样,心里那点褶皱似乎又深了些。“陈阿姨走的时候,是不是很突然?”
“说是急病,”老太太的声音低了些,“半夜里送的医院,第二天就没了。那时候俩丫头一个才十五,一个十三,哭得肝肠寸断的,街坊看着都揪心。后来好像是被远房亲戚接走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远房亲戚?李梅和林慧的笔录里都没提过。季洁记在本子上,打算回去查查档案。“那您知道她们母亲留下过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比如……一对玉佩?”
老太太想了想,拍了下大腿:“哦!你说那个啊!我听张奶奶说过,陈家大姐有个宝贝,是块能分开的玉佩,说要给俩丫头当嫁妆的,还说什么"平平安安"的。”她指了指石榴树的方向,“好像就放在屋里那个旧木箱子里,后来房子空了,箱子也不知去向了。”
从四合院出来时,巷口的修鞋摊还在,只是摊主换了个中年男人。季洁走过去,假装要擦鞋,和摊主聊了起来。摊主是本地人,在这里摆了二十多年摊,对陈家的事果然更清楚。
“陈大姐那人,心善。”摊主一边给鞋刷油,一边说,“那时候我刚摆摊,不懂事,收了个假币,是她偷偷塞给我五块钱,说别让家里人知道。她那修鞋摊,不光修鞋,谁家里有难处了,她总肯帮衬一把。”他顿了顿,“可惜命苦,走得太早。”
“她的两个女儿,您有印象吗?”季洁问。
“咋没印象?大的叫李梅,小的叫林慧,那时候总来摊前帮她递钉子、拿胶水。”摊主笑了笑,“李梅那丫头护妹妹,谁要是欺负林慧,她第一个冲上去。林慧就文静多了,总抱着本书在旁边看,陈大姐修鞋的时候,她就给姐姐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