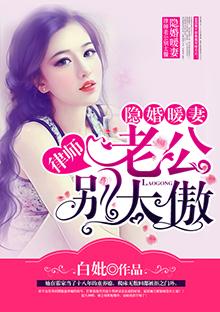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四旬老太守国门:对我精神不正常 > 第447章 我叫今胜昔十三(第1页)
第447章 我叫今胜昔十三(第1页)
那天晚上,篝火比平时亮了些。
今胜昔看着围在篝火旁的十二个人,看着老陈在给大家讲怎么修太阳能板,看着周以存给孩子递了块烤得焦香的兔腿,看着老医生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
废墟之上,秩序在萌芽,而希望,正顺着那些冒芽的小麦苗,悄悄长进每个人的心里。
……
虽然现在的天气不如之前那么极端,但是既然天气明朗动工土木肯定会遭遇袭击。
社区的存在,早已不是藏于荒野的秘密。
那盏彻夜不灭的警戒灯,在死寂的黑夜里如同跳动的心脏,既给幸存者带来希望,也引来了贪婪的窥探。
起初只是三三两两的流浪者,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中带着对秩序的渴望,像老陈那样的退休教师,会主动帮孩子们整理临时教室。
可随着人越来越多,一些不和谐的影子也混了进来。
有偷拿公共仓库罐头的青年,有拒绝参与巡逻却争抢食物的壮汉,胜昔不得不将接纳程序细化到极致。
观察期从三天延长到一周,由周以存带着两个老兵暗中记录新人的言行。
能力评估不再是简单问“会什么”,而是让他们参与搭建栅栏、筛选种子,看的是态度而非技能。
背景询问时,胜昔总会盯着对方的眼睛,从那些躲闪或坚定的目光里,捕捉言语之外的信息。
“社区不是避难所,是我们一起活下去的家。”
每次新人入社,她都会重复这句话,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那把磨得发亮的匕首——那是她从沦陷的家里带出来的,提醒着自己绝不能重蹈覆辙。
可该来的冲突,终究躲不过。
那天下午,太阳被厚重的云层压得喘不过气,远处的公路上突然扬起一阵尘土。
放哨的少年跌跌撞撞跑回来,声音带着哭腔:“来了!好多人!拿着刀和枪!”
众人涌到围墙后,只见七八个个壮年男子排成松散的队形,一步步逼近。
他们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裤,裸露的胳膊上刻着杂乱的纹身,最前面的男人扛着一把土制猎枪,枪管上还挂着半只风干的野兔。
“里面的人听着!”
男人的声音像砂纸摩擦木头,粗粝又刺耳:“把仓库里三分之二的吃的交出来,再把女人都送出来,我们就走。”
“不然——”
他抬手拍了拍猎枪:“这玩意儿可不长眼。”
恐慌像潮水般瞬间淹没了社区。
新加入的一对年轻夫妇紧紧抱在一起,女人的肩膀止不住地发抖。
几个老人拄着拐杖,脸色苍白地看着胜昔,眼神里满是无助。
今胜昔深吸一口气,踩着木箱爬上围墙,风把她的短发吹得贴在脸颊上,却吹不散她眼底的坚定。
“我们不会交出任何人,也不会放弃一粒米。”
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只有一片废墟。是我们一起挖井、种菜、搭建房屋,才有了现在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