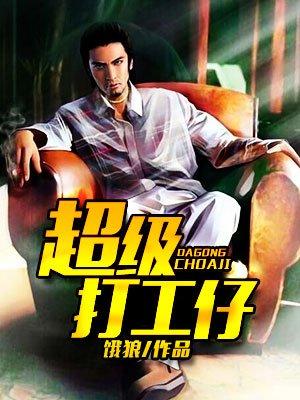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摇风记 > 第346章 共赴山河九(第2页)
第346章 共赴山河九(第2页)
温离看天色晦暗,终于在混战中下令,“撤!全部撤!往南门巷子!全部往南门巷子!”
祁岑离温离仅仅两步远,他听见几乎破音的嘶喊,在入夜的冷风里消散,他高声重复着命令,一路杀下墙阶,为仅剩的铁骑开路。
敌人乘胜追击,将铁骑咬死,不给他们生还撤离的机会。
断后的温离再想救人,也只能眼睁睁看落单的铁骑陷在敌军内,然后倒下去,淹没在攒动的人头。
白夜留意着城墙上的局面,零星的火把势单力薄,他看不清面庞,只见有黑影在阶梯上往下跑,接着他听见祁岑呼喊“向南门巷子撤离”,他当即转头朝死守的铁骑下了一道同样的军令。
早已在不远处待命的弓箭手终于能够拉起长弓,瞄准城墙的位置蓄势待发。温离下城墙吹响口哨,寒鸦渡飞奔而来,他骑上马疾驰向弓箭手列阵的地方策去。
到列阵前,他瞥了一眼后方的玄清司卫兵,充斥着血丝的眸子一敛,命令道:“除弓箭手外,其余人全部往南门巷子撤退!”
卫兵短瞬踌躇,方意识到马上的大人是在给他们下达命令,跟木桩似的杵了那么久的两条腿总算动了起来,提着腰间的刀撤往巷子。
温离调转马头,望着如瀑布泻下城墙的敌人影子,抬手一放。
就位的弦上弓如倾盆雨似的,布满半空,朝正下城墙和底下追赶铁骑的楚兵袭来。
温离皱着的眉在昨夜起就没舒展过,弓箭手继续上箭,他再次抬手,“放箭!”
在此处布设的弓箭手是为扼制敌军追击的步伐,当时梅鹤卿要突袭太恒以东,跟来的全是骑兵,骑兵的马就藏在离南门很近的巷子内。温离要切断楚兵紧咬不放的势头,这是撤出易州南门的关键点,为铁骑争取上马向南门突围的时辰。
楚兵受到一波箭袭,紧接着改变追击的目标,在黯淡的夜色里如一阵阵浓烟侵蚀而来。
这是温离与沙月事先的谋划,因此军备中箭支很大部分安排在这一节点。扼制是有成效的,吸引了楚兵的注意,甚至拖延住了冲杀的速度。
穹天完全黑了,易州内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光,弓箭手摸着黑向城墙射箭,而喊杀声却越来越近了。
温离下令整理箭篓,进行最后一次射箭。他不能让敌军压近,否则这些兵肯定来不及撤。
翻越城墙的楚兵没有马,冲锋唯有靠两条腿,在一波波阻挡的箭雨下像一具具肉盾,黑暗让他们看不清头顶的飞箭,耳边被铺天盖地的箭流声堵住,只能混乱挥着刀斩箭,不慎倒下就有挨后来者踩踏的危险。
没有马,对付一开始时蜂拥的敌军并不困难,温离也是见好就收,他不敢堵与楚兵的距离,纵然距离拉近对于弓箭手而言更能瞄准,但若是大军压上来,这点箭也是不够的,他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将箭用光。
“撤!”他拽动缰绳,转马头让弓箭手先向南门巷子跑,“弃掉箭篓和长弓!全力撤离!”
铁骑毫不犹豫照温离的命令去做,他们一边跑一边摔了弓,沿路丢掉解开的背上空空如也的箭篓,接下来的每时每刻都很紧迫,他们得抓紧时间了。
温离驾马殿后,铁骑跑进黑灯瞎火的巷子时,巷子俨然没什么人影,还剩没人骑的战马在原地等待着。
卫兵前脚刚至,提前在巷子等候的祁岑便命他们即刻上马,随前方仅剩的铁骑与南门沙月率领的部队汇合。
“哥!您不走吗?”卫兵里有人道。
祁岑也不耽误,“这是命令,突围只在一瞬,别拖军队的后腿!”
他走不了,白夜领上马的铁骑向南撤前再三嘱咐他一定要等温离,他也不是什么没心没肺的人,怎么能丢这大冷天冒着搜捕风险为他抓药的家伙在这而自己离开,他做过一次白眼狼了,可不能一错再错。
“您不走,我们也不走。”
“大敌当前别干这种拖后腿的事!”祁岑训斥道,“打仗就是要听军令,军令如山!”
卫兵也不愿祁岑为难,说了两句就跟上前头的铁骑。
马全一笼统藏巷内,骑上也不管是不是自己的,温离赶来后见有火把靠近,到马前定睛一看,说:“你怎么没走?”
祁岑孤身留下就是为等温离,“您没来,我哪敢自己先走。白夜领兵去南门了,后边没咱们的人了吧?”
“都在这了,走不掉的躲进屋舍里,看自己造化。”温离旋即高喊,“骑马上去南门!”
巷子里最后一批铁骑也浩浩荡荡走了,还有无人骑的马匹,在漆黑里甩动着马尾,等着那些再也赶不来的将士。
******
沙月在夜幕降临后退回南门内,将城门关闭,他与公子约定了汇合的时辰,下令士兵整顿,为汇合后最后一次突围做准备。
他大掌抹了把满是烟尘和血水的脸,靠在城门内侧的墙壁坐着休息,他的刀摆在一侧,刀身还挂着碎肉,他又捉起刀往地上来回刮了刮,把上头和血粘黏着的秽物都刮去,免得不够锋利,砍不死敌人。
忽然他双耳捕捉到城内传来的马蹄声,警惕心使他提刀站起身,“警惕!”
正给自己缠伤的孤华蓦地跳起来,捉刀的右臂受过箭伤,这一下又裂开了。
整顿和休憩的铁骑随之拎起刀面向声音的来源,混沌的黑夜里有疾驰的铁蹄向这里奔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