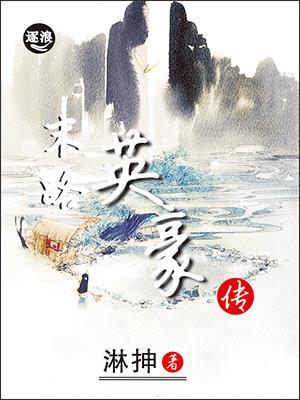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他却只想当驸马 > 69 关系(第1页)
69 关系(第1页)
越近年关越是冷寒。飞雪又起,路上行人不免小心翼翼,谨慎跌滑。一马车傍晚自城中行出,车内人不断催促着快些,全不顾忌前路有多难行。
城郊庄园,湖心暖亭。
一条临水而建的长廊直通暖亭门口,湖面宽广,冰冻覆盖,尚不能见一物,四下无处可藏。曾如易与万绅下了马车,被管家提着灯笼引到此处,只可见烛火印在窗上,屋内有一人影。
谢过管家,曾如易目送他缓缓而去,推门进去,响动只让里面的人微一抬眼。
“怀柯。”曾如易喊。
王怀柯目色又扫过万绅,谁也看不上似的,一言不发。
万绅又喊,她亦不回。这二人对视一眼,进屋关门,曾如易竟有些低声下气:“怎么了这是?”
屋里碳火正旺,桌上酒菜齐全,瓶里插的是才打了朵儿的白梅,没大物件,放不了什么东西。
曾如易环视一周,在王怀柯身边坐下:“我好容易求了人开恩才能见你一次,你是……受委屈了?”王怀柯这回嘲讽的轻哼一声,直接转过身背对他。
曾如易脸上挂不住,好在没有旁人,他只讪讪的。万绅看不过去:“大人这跟你说话,你好歹注意点。”
“是我求来的福气。”她说的抑扬顿挫,怎么听都是在阴阳怪气。
“穷乡僻壤里关了这么些天,出门出不得,见人见不着。”王怀柯有满心委屈,这会子不吐不快,“洒扫粗妇也敢对我呼来喝去。是,是我王怀柯天生命苦,不过幼时过了几年好日子,现在是随意是个人都能将我踩在泥底……”
她先是凄凉的说,到后来索性呜咽着,哭的眼前二人不知该如何去哄。
“这又是哪儿的话?”曾如易急忙问。
王怀柯这时一句也听不进去,捂着脸好不凄凉,那二人只好等她平静下来。
“我只要你一句话,你可还有能力救我出牢笼?”王怀柯定定的看着曾如易。
“我不不为救你放着京城的官不做十几年都待在琼州?不是为你这些天我用得着四处谋划求人只为见你是否安好?”
这些天压抑的曾如易也处处不得劲,求爷爷告奶奶的四处打点,求到这么个见面的机会,才见面便是质疑。
“你是做!好处呢?结果呢?”王怀柯“嚯”的站起身,“不止是你曾如易在琼州十几年,我难不成就不是了?”
曾如易抿着唇,王怀柯更加咄咄逼人:“我还有几个十几年能在这儿耗?”
一见面就剑拔弩张,万绅早习以为常,等这二人一个一步不肯退,一个一句不肯说,他便劝。
“好容易有机会见一面,就不要吵了。”万绅这段日子也不好过,被曾如易训斥的话还萦在心头,他实难报以真心。
仍是曾如易先服软,他执筷为王怀柯夹了她最爱的芋儿鸡,有些感慨:“我求了几次才求来的团圆饭,快吃吧。”
一听这话,王怀柯更是没来由的怒从中生。她指望着曾如易救命,曾如易求着别人只能吃口饭,这般迂回环绕低三下四窝窝囊囊,她实在看不清前路如何。
“这不是三十不是初一的,吃的哪门子团圆饭?”王怀柯还是稍忍一会,但她一向有气便撒,更何况现在面对的是曾如易,“我与你吃什么团圆饭?”
曾如易目色复杂,盯着王怀柯不语。
万绅其实也不解,曾如易是突如其来的喊他来吃这顿饭。王怀柯何时回的琼州,怎么回的琼州,曾如易又是如何知道王怀柯的去
向的,这些他一概不知。
但听了他们二人的对话,王怀柯能从京城回来应当不是曾如易的手笔。
王怀柯仍咄咄逼人。去京城前她还不信曾如易的话,什么护她周全不受委屈的托词她早已听的心无一丝波动。
但这次不同,路上她就感到自己暗中受到不少照拂,到了京城更是各种巧合,人数不对,提前散席的事情错开她的局,王怀柯深知曾如易办不到这些。
能办成这些的,恐怕便是他话中“求”的那个人。王怀柯思忖,能在京中有这番能耐还游刃有余的,不会是普通权贵。而这人肯花大力气去做这些,必然不是因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