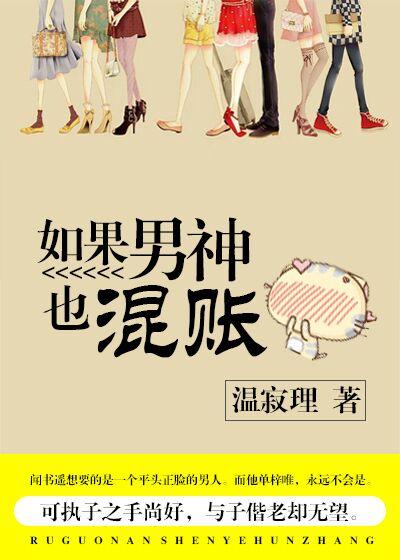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大师兄说过 > 232昔往矣八(第2页)
232昔往矣八(第2页)
孟君山目瞪口呆地望着师父,一时间忘了怎么说话。郁雪非看不得他的傻样,冷哼一声:“当这世上只有你会旅行不成?”
“那倒不是,”孟君山连连摇头,“只是没想起……”
没想起师父也曾经游历四方——他讷讷难言,未能将这话说出口。虽知道师父在拜师毓秀前也有过一番际遇,但那毕竟离他太过遥远,而他所见的师父总是沉心修行,在师父身边,仿佛岁月都要走得慢一些,与山下那俗世红尘更是毫不相干。
郁雪非并不在意他的胡思乱想,说道:“世间万物,皆令人有所感悟,你潜心创造是好事,只是别太过自满,以为天下除你之外没人更聪明就是了。”
敲打完尾巴翘太高的弟子,他随手在水球上一划,要将这术法散去。
孰料,那灵气凝成的镜像却一下子迸裂开来,远超那小小水球容量的激流喷涌而出,顿时在花房中下起一场虚幻的骤雨。墨迹仿佛被日光烧熔,从中流出生动的景致,山色苍青,树影葱茏,峡谷间河流曲曲弯弯,将万千色彩融化其中。
屋中两人,仍旧是一坐一站,置身于窄窄一条江面的竹排上。敲冰碎玉的瀑流声犹在耳畔,眼前那垂入江中的翠枝,叶片上水珠都纤毫毕现。
站在船头的孟君山头上扣了了个斗笠,一脸尴尬:“这个,本想给师父一点惊喜,但是……想必师父既然去过,也不会觉得新鲜……”
后半句越说声音越小,最后彻底没音了。
郁雪非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会,把孟君山看得头皮发麻,手指头直哆嗦地想要撤掉这幻术,忽然听到师父说:“竹排却是没坐过。”
孟君山一怔,抬眼看去,见师父已经转过头,望向了江水倒映中的远方。
……
“进来。”
孟君山在小楼前踟蹰,忽听到里面师父发话,顾不得犹豫,举步入内。窗上一簇簇重瓣紫花垂落,花色如雪,近看只略带一丝紫,风情尤为凛冽,令人仿佛能嗅到此地之外的寒风。
从花枝下走过,他拍了拍两颊,好让脸别那么僵。
枝叶环绕的屋中一角搭了张小桌,桌上摆着茶盏,像是待客后还没收走。孟君山回来一路上没见到门中有客,来拜见师父前又磨蹭了好一会儿,可以想见这客人已经离开许久。
即使如此,师父也似乎没心思管这些,径自在原处沉思。
孟君山上前收拾,重又沏了茶来,郁雪非摆手让他坐下,这才抬头看了他一眼,皱眉道:“在门口转来转去的,怕进来挨骂?”
“请师父责罚。”孟君山老实道。
郁雪非冷淡地说:“你的传讯我已看了。和正清的后辈起些冲突又如何,又没打输,也值得你放在心上?”
孟君山赔笑:“就是让正清的师兄弟们大失面子,唯恐让师父为难。”
郁雪非不耐烦地一挥手,懒得解释,显然在护短一事上相当不分青红皂白。他端过弟子奉上的茶,说了一句:“正清的人刚来过,既然他们没告状,那就是打得还不够重。”
“……”
孟君山这才知道:“原来先前的客人是正清来访?”
郁雪非略一颔首,看起来却不准备多提了。孟君山陪师父坐了一会,照例说些出行时的见闻,他口才不错,比起吃这碗饭的说书人也不差什么,又兼行路时常去绝景胜地,见识些奇人异事,讲起来也都是妙趣横生。
此番滔滔不绝,在外头能叫听众悠然神往,驻足追问,换两杯酒喝不在话下。师父听了则不见什么反应,只是偶尔点一点头,饶是如此,他还是说得很起劲。
讲着讲着,他端起茶润润口,不防师父忽然问道:“你信中说,在燕乡遇到了谢真,如今怎么没听你提起?”
孟君山暗道糟糕,一不小心说得不自然了,当即笑道:“我那时急着进山,与谢师弟见了一面就作别了,也不曾盘桓太久。”
郁雪非看了看他:“你们没闹什么别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