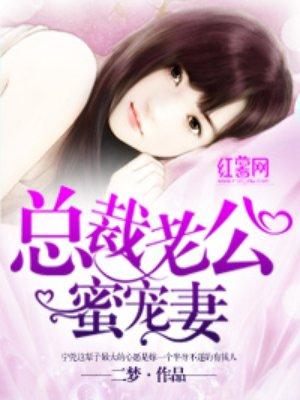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朕真的不务正业篱笆好文学 > 第一千零六十六章 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第4页)
第一千零六十六章 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第4页)
这个一石三鸟的纲运制,组成的纲商,就会完全垄断盐的运输。
以前谁都能往边方运粮运盐运货,在卫所换取白银,可是有了纲商,就有了入门的门槛,只有朝廷照准的几家商贾才有权运货。
这就是一石三鸟的第三鸟,对纲商直接征税,简单直接。
日后,纲商们想送,边方才能收到如同毛毛雨的物资,他们不想送,把盐之类的卖到腹地,而非边方,那边方什么都没有,连盐都没有几口。
垄断的苦没吃够,还要再吃一遍。
大明商贾愿意把货物送到边方去,是因为边方有朝廷发的银子,才肯到边方去,如果真的把这个权力给了富商巨贾组成的纲商,大明的边方,只会彻底糜烂。
“把这个李汝华送到绥远去垦荒,种三年地,就什么都明白了,坐在京师的衙门里,对着边方,指手画脚,谁给他的胆子!不了解情况随意指指点点,连朕都不敢这么做!”朱翊钧给了明确的惩罚,先送绥远种三年地。
干点活儿,脑子就清楚了。
至于两淮盐运使袁振,他倒是和这个李汝华不太一样。
袁振是希望往边方运更多的东西,他的想法是:恢复之前的开中法。
随着开陇驰道的修建完成,运输能力和费用大幅降低,能不能借着开陇驰道的便利,恢复祖宗成法。
他的想法很好,但这是痴心妄想。
有些政策被破坏了,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但凡是开中法有一点恢复的可能,王国光就不会把白花花的银子都给边方。
这可是每年660万银的超大规模支持,一年11个先帝陵寝了(最开始用了50万银,后来修缮补了10万银,一个先帝陵寝是60万银)。
如果有机会,朱翊钧当然也希望可以恢复开中法,可惜,政策已经在孝宗年间,被破坏的干干净净了。
《尚书》有云: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
这个世间就是如此,一旦做出了决策,不是说你懊悔了,就可以改回来的,往往都是悔之晚矣。
朱翊钧对每个政策都很谨慎,一看事不能成,就收回成命,甚至很想很想做的事,却要等很久很久,才会去做,就是怕自己错误的决策,给百姓带来深重的困难。
“咦,浙江商帮,整天在松江府作甚,他们不应该在宁波市舶司吗?”朱翊钧拿起了松江知府胡峻德的奏疏,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松江府商帮大乱斗,甚至比安南的五主七十二家大乱斗,还要乱一些。
“不仅仅是浙江几个商帮,连山西的商帮,都在松江府。”张宏专门去了解了下这个情况,情况十分复杂。
晋商、黔商、徽商、吴商、扬商都在松江府,和松江府本地的远洋商行,展开了极其激烈的竞争,甚至松江远洋商行,差点就被这几家联手给取而代之。
甚至斗出了几分逐鹿中原的气势,松江府这个好地方,有德者居之!
孙克弘长期投资松江海事学堂,在上海大学堂营造的时候,孙克弘还捐了五十万银,不求任何回报,只求借个善缘。
海事学堂的舟师、上海大学堂的学子,毕业后,也都念这份香火情,若是条件一样,都会投效松江远洋商行做事。
若非如此,几家联手,松江远洋商行,真的不是对手。
人才这东西,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胡峻德上奏,主要是说松江远洋商行的人选问题,孙克弘没有推荐他的儿子继承商总,这是几乎让所有人都预料之外的事儿。
孙克弘推荐了他手下的精兵强将。
一个楚地来的外乡人,名叫陈敬仪,这个陈敬仪是长沙人,家里一穷二白,本来在孙克弘的棉坊做学徒,别人都叫他六子。
这个六子不得了,短短十二年,就从学徒执掌了孙氏所有的棉坊,到万历二十二年,陈敬仪已经成了孙克弘最倚重的手下。
孙克弘倒是想举荐自己的儿子,但思前想后,最终向朝廷举荐了陈敬仪,他有能力、有担当能带领松江远洋商行继续向前走。
他考虑问题,主要是考虑到自己儿子,没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因为一些财货的纠纷锒铛入狱,恐怕他们孙家,就真的成了上海滩的大笑话了。
“希望这个陈敬仪,能够不负孙克弘的期望吧。”朱翊钧朱批了这本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