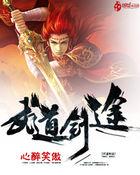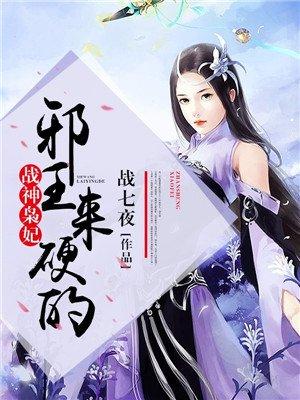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燕食记月饼 > 第四章 风起河南(第3页)
第四章 风起河南(第3页)
锡允说,今年的海棠,开得迟呢。
颂瑛说,是啊,春寒久了,到现在才开了头茬。
锡允说,小时候,跟着大哥二哥读家塾。叔父请了陈桂生给我们讲《资治通鉴》。陈师父最爱海棠,知道太史第百二兰斋的海棠开得好,偏要等到花期才来教我们。叔父就在塾室给他摆满了。陈师父说,海棠好,好在无香。阖上眼睛,佛不动心;张开眼睛,又是满目翠艳。这一阖一张,就是《资治通鉴》里的所有了。我愚钝,至今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大哥二哥,一个做了国会议员,一个做了省议员。我到现在,只记住了海棠。
五举山伯,曾向我展示他在广图所得的成果。
有一份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粤声报》的复印件。其中一则新闻,是关于前一日在苏州举行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粤声报》对整个公祭仪式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刊登了“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告全国民众书”。此次设坛公祭,到会军民共计五万余人。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会代表居正担任主祭官,陪祭官为国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在这份报道中,也选载有全国各界名人发来的挽联。其中一则发自广州,全联为:
白日阴明,愁魂黯黯,我辈哀怜冤忆。崇拜英伟,痛今朝追悼九泉,哭沉天地;
咒持等等,磬叩声声,人生得尽招升。皆大欢喜,愿此后轮回再世,整顿乾坤。
具名为“向翃胤”,一目了然出自太史的手笔。但当他撰写这则挽联时,十九路军已为南京政府所迫,撤离上海抗日战场,被调派往福建。一九三三年秋,蔡廷锴等将领在前线与中共展开和谈。次年十一月,蒋光鼐、蔡廷锴与邓世增等发动“闽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调集八个师入闽,重兵镇压下,“闽变”事败,蔡廷锴等高级将领辗转香港,部下谭启秀等参与者皆被开除军籍。谭启秀猝然回粤,寄居于太史第,半生戎马生涯就此告一段落。而其副官向锡允,却在战场上不知所踪。这都是后话。
我带着这份载有挽联的报纸,向荣师傅询问当时太史第内的情形。他看一眼,想想,摇一摇头,似乎不愿提及。但大约终究忍不住,对我说,如果阿妈不做那一餐饭,以后可能就都不一样了。
向太史中年参佛,暮年皈依受戒。太史第内设坛追悼淞沪亡勇,请了弥陀寺的云禅法师亲自来做法事。三太太便说,不如在法事之后,办一场素宴,也用以酬答义款捐赠的应援各界。
此时的太史第,宴客排场自当不如往日。太史意得时,盂兰节大放水陆三宝,唤紫洞艇四五,诵经开坛,年年烧幽,太史第上下至戚友以此迁兴,达旦通宵,山水环回,完坛始归。向晚思之,方觉镜花水月。
他便嘱咐下去,这场素宴,不妄奢华,重在周到体面。太史第以蛇宴闻名岭粤。但因太史多年礼佛,众位太太亦追随,府内初一、十五与佛诞必守斋。故而太史第的素斋,其水准与外名斋相较不遑多让。几位家厨,可谓各擅胜场。利先善做蛇宴,冯瑞工中式白案,莫子项由“十三行”法餐室礼聘而来,专责西点。而做素斋的,就是府上唯一的女厨来婶。
说起来婶的口碑,其人之势利在太史第里是出了名的。但因做人圆转,且得三太太宠信,自然在一众仆从里,有她的地位。当然,三太太用人向以务实为原则,也是赖得她的厨艺。
府里的人说来婶投其所好的功夫了得,是有出处的。三太太的生辰在农历六月底,太史第有道当家的素菜叫“三宝素会”,一听便知为其度身订制。那时兰斋后的水塘,菱角正上粉。皮青中带赭红,里头嫩得掐汁,刚刚可以剥肉,与鲜草菇和丝瓜块同烩,加个琉璃芡,不需佐料提味,已是齿颊留香。火候重要,出锅时那菱角嫩滑,咬一口清甜如蜜。原料是应时的,并不稀罕,意头却是四两拨千斤。这“三宝素会”,太史第的人吃了十多年,眼看着三太太的地位日隆。那做菜的人,自然言语行事,也都十分气壮了。
可若说来婶的首本,是为太史第撑足面子的“鼎湖上素”。既是首本,自然不惜工本,“三菇六耳”缺一不可。再加之鲜莲子、百合、冬笋、炸生根等料,用素上汤以文火煮上三个时辰,再以大火同炒。听起来工序并不复杂,可功夫都花在备料上。因竹笙、榆耳等都出自野生,桂花耳更是朝发夕萎的稀罕物,在外采货的厨工,有时不免疏忽些。可但凡有一味不合了规矩,或以次充好,来婶先将他们祖宗八代问候一遍去。
按理,精益求精是不错的。这用料的讲究,多少也是太史第行事的分寸。再说其素菜的料,无非是腐皮、面筋、生根,新鲜的水豆腐、板豆腐、布包豆腐及硬豆腐,每每万变不离其宗。佐料也不可大鸣大放,葱、蒜、韭、薤及兴渠,所谓“小五荤”,自然用不得,偶也用豆豉便打了大折扣。酱料多用面豉、酱油、南乳及腐乳。而来婶的心得,提味全靠各种菇类。用的居多是冬菇和干草菇。因为用的量大,这洗涮晾晒的工作,便都落在厨工身上,动辄得咎。有敢怒不敢言的,就编了个歌诀,“冬菇草菇荔枝菌,香菇松茸鸡肶菌,隔篱利先唔开口,姣婆分分黐孖筋。”再隐晦,听者也知道说的是大厨利先叔和她的事。
利先有个老婆在乡下,人虽非君子,在厨房里打情骂俏可以,但却也不想招惹是非。可暧昧了大几年,经不住寡居的来婶穷追不舍,竟将那发妻给休了。但成了“一支公”,他却又硬了颈,就是不和来婶摆酒,所谓“拉埋天窗”。这以后,来婶的脾性便越发不可收拾。仆从间流传了一个笑话。当年守长斋的九太太青湘,爱吃一道“桂花锅炸”。做甜锅炸要用上牛奶和鸡蛋,这两种虽属花素,但食清斋的人是忌口的。因彼时九太太极受太史宠爱,后厨便专养了一笼东竹母鸡,生下的蛋不受沾染,才可入馔。可有一日,厨工未关好鸡笼,竟然让这几只母鸡跑了出来。后厨原有一只鸡公,大约也是垂涎已久,来个霸王硬上弓,将这几只鸡娘纷纷临幸了一遍。发现时已经迟了。这可也让来婶看到了,拎起把菜刀,风火火地出来,一言不发,将那鸡公拎起来,照颈子就是一刀。临了将那鸡头,扔在地上,唾一口道:“贱格!”这真是迅雷不及掩耳,那鸡身子喷着血,还拍着翅膀,在地上扑腾。看得后厨上下,惊心怵目。有人便私下里说,真是阿弥陀佛,鸡公这一刀,是替利先叔挨的。利先闻风而丧胆,此后和来婶,连眉来眼去也不敢了。
因为有三太太撑腰,来婶向来恃宠而骄。再加上为情所乱,对后厨的事情,渐渐不上心了。无奈太史第近两年,是多事之秋。事事敷衍,也就有些粗枝大叶。有次四房的近身来端药膳,看见来婶做罗汉斋,大约是手边老黄豆熬的素上汤没了,顺手就舀了一勺近旁的鸡汤做底汤。看见的人,知道她的厉害,自然不敢声张。
后来,逢到初一、十五,要开素斋,她大约也是惫懒了,除了一两个主菜,其他的,她竟着人到龙津路上的“盈香斋”买了现成的来,热了应付主子。终于有人不忿了。三太太便当着众人的面放话说,我养兵千日,要放在大处用的,是用来佛诞上给我撑场面的。
原本,这酬募后的素宴,便是三太太说的大场面。她自然没想到,会自打了嘴巴子。来婶竟就在前一天夜里失了踪。问起来,说是有急事,回了佛山老家。
三太太哑巴吃黄连,心里恨得直咬牙,最恨自己将人骄纵坏了,这可难收拾。表面上,却还是一副风停水静的模样,一边着人去外头借厨。
这事还未传到太史耳中。此刻,太史正和云禅法师在书房里头。法事将至,因是告慰英灵,二人都格外郑重。旁的人都不敢进去打扰。
出去借厨的,无功而返。这火急火燎的。三太太点了名字的厨师,无论是食肆还是府第,竟一个个都挪不开身。能出来的,她又看不上,怕败了事。终于,她也有些慌,早知如此,就请云禅带了净念来,现在好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后厨都哑声,这净念和尚,是六榕寺榕荫园当家厨僧。其声名之大,连当年陈济棠的持斋夫人莫秀英都三番延请。可他却有个习惯,不涉军戎,就是不肯踏陈府一步。不知怎的,倒是与太史颇有佛缘,十分谈得来。三太太便着来婶与他习厨,即使不太情愿,他还是教了几个拿手的菜式。“雪积银钟”“六宝拼盘”“佛蒲团”,都是广府四围的素菜馆所没有的独一份。这也是三太太将来嫂捧在手心里头,看不上外头厨子的缘故。如今可真是釜底抽薪。
六神无主间,她想想阖府能帮她拿主意,又不落话柄的,竟只有一个大儿媳。于是找了颂瑛。颂瑛想一想,说,三娘,那我就给你荐个人。
慧生来了,往三太太跟前一站。三太太打量她,扬起下巴,问道,你会做素菜?
慧生愣一下,张口答道,嗐,太太抬举!我一个粗手笨脚的下人,哪里会这细巧东西。
说着眼睛便往外头看,是想要脱身的架势。颂瑛便说,慧姑,太太问,自然是咱家落了急。你从前在老家,给老姨奶奶做的那几样,应付得来的。
此时三太太也硬颈不得,口气软了下来,说,你好歹做上几样热菜,精粗且不论。先替我敷衍过去。
慧生站在了太史第的厨房里。她的手触碰了一下灶台。云石的凉,顺着她的指尖蔓延上来,一点点地。却出乎意料,最后有一丝暖,让她心里悸动了一下。
她不再迟疑,对身旁的厨工说,烧水,备料。
那日赴太史第素宴的人,大约都有挥之不去的记忆。他们记得筵席的最后一道菜,端上,是一整只冬瓜。打开来,清香四溢,才知里面别有乾坤。浓郁的花香之下,可见鲜莲、松茸、云耳、榆耳、猴头等十味素珍,交融浑然。尝之,其鲜美较“鼎湖上素”,有过之无不及。来者交赞不已,连云禅法师亦啧啧称是。问起菜名来,说叫“璧藏珍”。
这一道,慧生用素上汤文火炖了两个时辰。她静静地候着,待火候到了,她对阿响说,仔仔,去兰圃给阿妈摘两朵栀子来,越大越好。
慧生将云白的栀子花,轻轻掰开。后厨便是一股四溢的浓香,随着雾气蒸腾的热力,击打了她一下。那花瓣的触感厚实,滑腻温存。忽然间,她觉得自己的手,是被另一只手执着,牵引着,一点点地将这花拆成了瓣,落到这汤水中。变色、卷曲、沉没。她想起了,她回忆起了那个溽热的六月,满室的栀子花香。清晨,那个人用水净般的目光看着她,告诉她,他终于还是走了。没来得及话给他听这菜的名字。
这名字,自那人唇齿间轻轻吐出,叫作“待鹤鸣”。
此时接近饮宴尾声。人们未解朵颐之快,有人忙于言商,有人捭阖时事,有人谈到激越处,不禁慨叹,抚案潸然。然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位耆绅,在人群中一言不发,反复地品尝这道菜。他闭着眼睛,半晌,忽而嘴角抽动了一下。
他起身,借故离开了饭厅,走进了太史第的庭院。太史第的人,看到一个老者,在各处游荡,甚至深入一些少人去的角落,似在各处逡巡。但因为他的穿着体面华贵,举止亦无逾矩,人们便也由他去了。他在每一处流连,眼中热烈而谨慎,如一头年迈的猎犬。终于,他在百二兰斋停住,目光落在正随花王捉虫的阿响身上。他静静地打量阿响,由头至踵,眼睛似乎再也无法挪动。久后,他似乎下了一个决心,毅然转身离开。
荣慧生,这个大少奶的近身阿姑,在太史第的筹募素宴后,获得了无上的声名。人们的结论是,如太史第钟鸣鼎食,即使日后寥落,仍是藏龙卧虎。哪怕一个不声不响的仆妇,亦不可小觑,必内藏乾坤。
在这之后,慧生再无意庖厨。她甚至尽量减少去后厨的次数。为颂瑛准备消夜和药膳,她会去小厨房。这是让她感到安心的所在,是她自己的一方天地。如同以往在何家,也是如此。在这方天地,她可释放她的手艺,这手艺藏着她的过往。而她释放所得,足以俘虏一干人的味蕾。其中包括颂瑛那个口味乖张的老姨奶奶。颂瑛的祖父去世后,这老人将自己关在没有光的后厢房里,布置为佛堂,青灯持斋。她唯一与外界的交流,就是颂瑛从小厨房给她送去的素食。颂瑛对这个姨奶奶有别样的感情,她知道自己的父亲庶出,自这老人。但父亲很快过继给了太夫人,才有了她一脉相承正房小姐的身份。但出自血缘的亲近,令她们有着相似的食欲。是慧生的手,无形中养刁了祖孙二人的舌头。于是,慧生将这些带到了太史第的小厨房里,成为主仆之间的默契与秘密。“海棠片”“素云泥”“增城笋脯”“雪梅饼”,这些只会属于颂瑛。太史第其他人等,哪怕亲近如五小姐,也不可染指。
但她没有料到,素宴尾声,那道叫作“熔金煮玉”的白粥,收服了太史,令其心驰神往。他通过三太太与颂瑛商议,即使不深入后厨,但希望慧生负责府中的粥品。慧生犹豫了一下,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