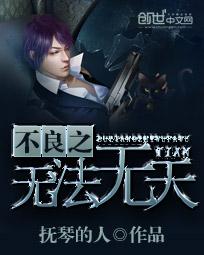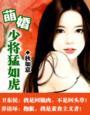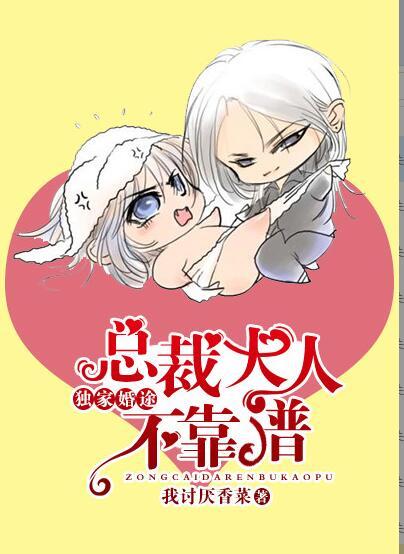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燕食记月饼 > 第八章 月满西楼(第4页)
第八章 月满西楼(第4页)
在一个夏夜,我和荣师傅师徒看了五十周年纪念版的《帝女花》。我们在北角的一间糖水铺消夜。感慨间,我问他老人家,荣师傅,你说,一个师父真的会容忍他的徒弟,拥有和他同样的才华吗?
荣师傅哈哈大笑,说,才华,只有你们文化人才会这么说。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你问陈五举,他要是不改行做上海菜,凭他整得一手好莲蓉,我做师父的仲可以揾到食?
五举山伯,正在细心地将一些黄糖,撒进豆腐花。这时抬起头,憨厚地笑笑。
我便又以向宋二人问他。他眯起眼睛,好像望着远方,目光却落在糖水铺的标价牌上。他说,那时候,我爱看七少爷度曲,好像剧本早在心里头,一边唱,还有做手,一边走来走去。他要写曲,不是念出来,而是唱,好像在台上演大戏一样。唱着做着,一晚上就是一个本子。要是找人抄曲,没人能跟得上,都给少爷骂出了门。可那天晚上,阿宋来了,少爷唱一句,他便记一句,嘴里跟着数板。不忘音韵身段,倒好像与少爷是一个人。一个人分成两人身,就这一唱一和,“查、笃、撑”“查、笃、撑”,一折戏就记下来了。什么也没耽误。
我说,那还有呢?
荣师傅说,还有啊,就是我做的饭喽。阿宋最爱吃的,是腊味煲仔饭。
那个夜晚,太史第响起了久违的笑声。在这初夏的夜风中,飘荡不去。阿响看着少爷在笑,不禁心里有些酸楚。自从与颂瑛仓促而别,音讯杳然。他似乎就不曾笑过。他只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度他的曲。他有时会托付阿响将写好的本子送到固定的地方。阿响固然知道,这曲词的铿锵之音,是全然将自己置身度外的。这是个天真而勇敢的人,乱世的悲喜于他,太过复杂而沉重,他唯有唱出来,写出来。却再也无法为之一笑。
此刻,锡堃朗声大笑,笑得如此由衷。阿响看着被少爷称为阿宋的年轻人,只是微笑,眼灿如星。听七少爷微醺后,说着些“痴人疯话”。
待到后半夜,阿宋起身告辞。锡堃已酩酊,踉跄着起身,却又坐了下去。远远对阿宋说,你方才那段“扬州二流”,我总觉得末句还缺了力道。待来日……来日……说完这句,他便坐下去,歪着脑袋睡过去了。
旻伯便道,唉,又喝成这样。响,我扶少爷进去,你送一送宋先生吧。
在苍黑的夜里头,两个人默然地走,走到龙溪首约的路口。阿宋开口道,今天真要谢一谢你。
阿响说,谢我做什么。
阿宋笑一笑,不是你对我说,听日再来过,我可能狠不下心来,唱一出破釜沉舟。
阿响也笑,说,我是好心怕你累,倒成了激将了。我书读得不多,可知道一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瞒你说,当年我拜师父,也是用了和你一样的法子。
阿宋说,哦?那我们倒有缘分了。你方才做的腊肉煲仔饭,很好吃,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味道。
阿响就挠一挠头,说,那真是歪打正着。其实是冬天剩下的腊肉,我是不想糟蹋东西。你老家是哪里?
阿宋望一望远处,说,香山。我很小就出来了,去了上海读书,可舌头都记得呢。我们家不富裕,这煲仔饭要年节,阿妈才会做给我吃。
阿响喃喃说,香山。
阿宋说,是啊,也是孙先生的老家。你知道,我有个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为孙先生写一出剧,演给天下人看。
阿响说,一辈子才刚刚开始,说什么有生之年。
阿宋笑笑,这也不打紧。是我小时候,有个看相的,给我算过一卦,那卦辞我还记得呢……罢了,我能和七哥学上戏,还说什么往后呢。
阿响说,我们家少爷,嘴上恶声恶气,心里是极善的。
阿宋过了一个数板,轻轻唱道,女儿香,断人肠,莫道催花人太痴,痴心赢得是凄凉……谁说不是,心里不善,哪里写得出这样的曲子来。
阿响顿一顿,便说,如今少爷写的,倒不是这些了。他是个不管不顾的人,你跟了他,不要怕。
阿宋低下头,又抬起来,看着阿响,眼里是灼亮的。他说,其实我想拜他,倒是因为在香港时,他作了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其中一句,“曲有百工,兴邦惟人。”
他便站定,对阿响说,就到这吧。这太史第可真大,我们绕了整条街,还没走到正门呢。我慢慢走回去。
阿响便也站定,看这青年人渐渐走进夜色中。因为时值十五,天又晴。月亮澄明,还有满天的星斗,夜并不黑。他走了很远,身影也仍能清晰地看见。
安铺的信迟迟而来。是慧生的口气,说是家里一切都好,叫他勿挂念。日本人的飞机比往日来得少了些,他们商量着去广州湾暂避,叫他在得月阁多留些时日。阿响读下来,眼前却浮现出叶七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信里只字未提,要他在广州找的人。亦未提到秀明,催他回来完婚。只说,有些手艺要留着,待天凉下来,从长计议。
转眼到了端午。“得月”收得早,过午即打烊。
照例端阳这日,珠江上有扒龙舟的风俗,上午是趁景。起龙、拜神、采青、划船、吃龙船饭、入窦,忙了一程子,午后才是“斗标”的正印。穗上的好男儿们,摩拳擦掌,一展身手。这也是整个广州城里的热闹,万人空巷。商铺食肆,便也偷得半日闲。
阿响虽非爱热闹的脾性,可想起上次看扒龙舟,还是七八岁时,便也随茶楼里的年轻伙计们,去热闹了一程。回来“得月”,天竟已薄暮。伙计们一边议论,一边摇头说,到底还是时势不济,连这龙舟都不及以往好看了,强打精神似的。
拾掇一番,伙计们打了烊。阿响想着,世道再不济,怎么也是回到广州来的第一个节日。心里挂着,便拎着一挂长粽,往太史第回。
刚从边门出来,迎脸便遇上一个人,朝茶楼里望。
他见这人面善,便说,先生,我们收工啦。
那人“哎呀”一声,说,紧赶慢赶,还是迟了。
阿响听他的粤白里,有浓重的北方口音,也不禁停住了步,问,有乜帮到你?
那人抬一抬头,说,唉,逢上端午,我们这些异乡客,不就图吃上一口得月阁的粽子吗?也算囫囵过个节。你说我好好的,去看什么扒龙舟。
阿响就笑了,说,我们上晌就关门了。您要是赶来买粽子,倒又耽误了看扒龙舟。
那汉子便袖起手,叹一声,说,小师傅,你们本地人,年年吃得看得,哪能一样呢。
听他这么说,阿响心里一动,便也喃喃道,您要这么说,我离了许多年,也算不得道地广州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