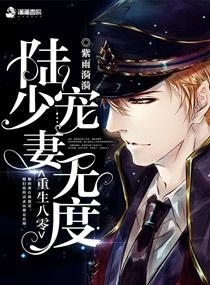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燕食记月饼 > 第十二章 戴氏本帮(第9页)
第十二章 戴氏本帮(第9页)
那还消说,我这里的大厨,红案白案,文武双全。明义听他夸下海口,在心里默默流汗。
明义到后厨去商量。五举想想说,我来吧。
上来的是一道生煎。上面撒了芝麻粒儿和翠绿的葱花,焦黄的壳,看上去让人食指大动。夫人看看说,好是好,终归还是一道生煎。
明义便附在邵公耳旁说了一句。邵公便道,哈哈,内里有乾坤。
夫人便搛起一只,轻咬一口,才发现,这生煎的皮,不是用的发面,而是透明脆薄,里面有汤汁流出来,极其鲜美。再一口,原来内藏着两个虾仁。还有一些软糯的丁儿,混着皮冻化成的卤汁,咬下去十分弹牙爽口。夫人品一品,眼睛亮了亮,说,你们快尝尝。这花胶,用得太好。
众人下箸,纷纷称是,都说,想见一见这位点心厨师。
明义便引了五举出来。夫人说,你这道生煎,皮用得很讲究。
五举说,用的是水晶粉,混了澄面。先蒸一道,然后才下锅煎,所以外脆里软。
夫人与她先生相视,笑笑说,虾饺的制法,弗得了。这花胶粒儿,也是你的主意?
五举点点头。
邵公也得意,说你们不知。我这点心师傅,别看后生,可大有来头。原是同钦楼荣师傅的门下高足。如今和我干女凤行结了姻缘,做了上门女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明义没料到,邵公会说到这一层,便借机上菜,让五举退下。
可客里有一个却恍然道,啊,是“莲蓉王”荣贻生吗?听说传了一个徒弟也是整了一手好莲蓉。不知我们有没有口福?
邵公一乐,说,那还在话下?明义,请你女婿给我们几个老的,做一笼莲蓉包吧。
明义看看五举,眼神里黯然下去。没待他开口,五举跟几位鞠一躬,说,我不会做。
转身便走了。
食客们面面相觑。邵公何曾给人这么抢白过,也是动了气,一拍桌子道:
戴明义,你这个女婿太不识抬举,愣头青!
五举将邵公给开罪了。
明义着小两口上门,给老人家赔不是。但凤行说,不去!我五举没有错。有也是功过相抵。这伙子有钱人,口味刁钻不怕。可到本帮菜馆点广东点心来吃,不是触人霉头吗!
爹,我且立下规矩。五举以后不上铺面见人。要见,我来见!
但那日五举创制的“水晶生煎”,就此便成了“十八行”的一个招牌。即使多年后,别的上海菜
馆,想要如法炮制,可偏就做不出五举的味道。
后来有人说起五举山伯。说五举不是山伯,是杨过。自己废了“大按”一条胳臂的武功,剩下“小按”,依然耍得起一手出神入化的独臂刀。
凤行呢,便是小龙女。教得五举,也伴得五举。两个人算是琴瑟和鸣,将“十八行”的声名,渐渐打开了。以五举的灵,一年后,已将本帮菜烧得轻车熟路。只是落料么,还稍保守些。凤行快人快语,是不迁就他的,常说,放酱,加糖。不吊糟,这味怎么能出来呢?
闲下来时,五举便好自己琢磨,又做了几款新的点心,比如“黄鱼烧卖”“叉烧蟹壳黄”。懂行的,便看出是粤沪合璧。只这闲情所得,倒很有成就,慢慢传播开去,成了食客们饭中必点的主食,便让“十八行”在港岛再不同俗流。
明义与素娥,很是安慰。他们都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老了。一爿家业,到底是指望上了一个闺女。人说巾帼不让须眉。戴家的巾帼却引来了一个须眉。阴阳而来,乾坤定海。
明义夫妇,在此后的数年,其实错过了小儿子的成长。
戴得是这家里的异数。三岁来港,对在上海的生活了无记忆。他是实实在在在香港长大的孩子。对这城市的感情,与他自己的成长同奏共跫,休戚相关。上海,对他只是个幻影,代表着他父母的根系。哪怕多年后,他回到了家乡,也如过客。“杨浦区通北路37号”,是他们在上海的门牌,也只是照片的背面的一行字。一笔一画,冰冷无温。
在家里,他的父母与兄姊,总是讲上海话。他会讲,亦会听,但总觉得与自己隔了一层。这种语言有某种魔力,可以在人群中辨认彼此。他记得,在北角成长的岁月,他的家人在任何场合,和陌生人相遇,大家说着广东话。但凡有上海人在,便迅速捕捉到对方话语中的蛛丝马迹,改用上海话亲切地交谈,而不必顾及旁人的在场。年幼的戴得,因此会觉得尴尬,甚而羞愧,好像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代表。
他自认是个香港孩子。然而,比起生长于斯的本地孩子,他仍然是孤独的。家人的存在,一直在提醒着他的来处,也影响了他的口音。读书时候,同学们总会嘲笑他的口音。他的广东话里,带着上海的腔调,甚至还有福建话惯有的尾音,这是他少年生活在北角的印记,很多年都摆脱不掉。在语言上他是有些迟钝的,他总觉得自己不及兄姊聪慧,或是因为老来子的缘故。
这些都造就了他身处奇异的边缘。在试图努力了许多次后,他终于放弃。因此,他让自己养成了一种看似不在意、信马由缰的性格。他用这种性格,抵御周遭令他感到压力的任何东西。他的父亲明义,怀着某种对自己青年时期的执念,将他送进一所英文学校。但他很快开始逃学,因为这所学校向上的氛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逃学,无知觉间,开始了在学校附近的游荡。
他发现,他很喜欢游荡。在游荡中,他让某种紧张的东西释放。湾仔是很适合一个人游荡的地方。他沿着叫作庄士敦道的电车道漫无目的地走,看到一条横街巷道,便随即拐了进去。这一带,是“二战”前发展的住宅区,克街等地能看到许多战前的旧楼。而太原街、交加街、湾仔道一带仍有传统的街市。戴得的心中,有一张漫游的地图。利东街的印刷铺,轩尼诗道的循道卫理教堂,星街的圣母圣衣堂,被称作夏巴油站的德士古大厦,都是这地图上的坐标。
还有太多地方,可以让戴得在游荡中驻足。修顿球场总有不少待业的人,或站或坐,在等待被人挑选。露天的表演,也可以让人看很久。从大王东街穿过去,便是洪圣关帝庙,里面有年老的婆婆,披散着头发,为人“打小人”驱邪。打小人的过程伴随着歌诀,极为漫长。戴得站在旁边,可以听上许多遍。大王东街与庄士敦道交界,是和昌大押所在。戴得远远站着,看着典当的人,各色的行止。踮起脚,将东西举到当铺的窗口。有的同时间,还四顾一下,用动物般警醒的眼神。当他走累了,便随机地走进一家戏院看电影。有时是“国泰”,有时是“南洋”或者“大舞台”。他其实并不很喜欢看电影。但是他享受在黑暗中,无人打扰的错觉。他看不见其他人,就当他们不存在。他们不存在,他便是君王。
走出影院,天已经半黑。他就在街边的大排档坐下来,叫一盘肠粉或炒牛河。这些大排档多半在马师道或史钊域道。他对着大街,看着路上的行人,慢慢地吃。他并不很喜欢吃家里的东西。此时“十八行”的本帮菜,在邵公等一众老饕的锻造下,已经日趋精致。但是,戴得自认没有高贵的味蕾,他的口味就是在与这些大排档的朝夕相处中,积累而成。
家里的东西,他唯一喜欢吃的,是凤行做的黄鱼面。
在家里,他亲近的人,是他的小姊姊凤行。自戴得有记忆,凤行似乎对他就抱有某种责任。
尽管那时,她自己不过是个九岁的孩子。但是,她与幺弟阿得间,有如某种母鸡护雏的关系。在外人看来,这种景致未免滑稽。北角的邻居们,还记得,在戴家门口,一个小女孩,吃力地把一个更小的男孩,抱在腿上。用他们所听不懂的上海话,在唱一支童谣,一遍又一遍。男孩渐渐听得有些不耐烦,身体出现了拧动与挣扎。女孩便更紧地抱住他,脸上带着近乎肃穆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