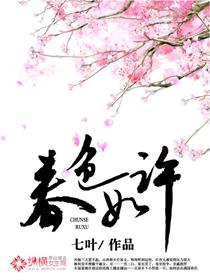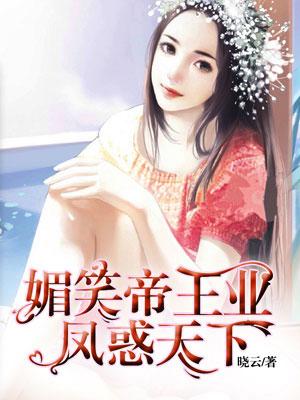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汉阙 笔趣阁 > 第583章 番外8 穿越者(第2页)
第583章 番外8 穿越者(第2页)
而自刘向从埃及回来后,又组织着任弘掳来的希腊学者们,开始对汉军从亚历山大图书馆中“保护”的四万多册书籍进行翻译。
这场翻译运动费时近二十年,基本完成了工作,希腊字母、象形文字变成了隶书,除了《几何原本》外,毕达哥拉斯学派、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希波克拉底医派的作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家们,其著作都被介绍到了大汉。
西方文明的果实,被任弘强行取来,摆在汉家士人面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希腊版“诸子百家”的成果中,确实有不少东西,值得吸纳为己用。
等石渠阁真正实现“世界知识大汇总”时,刘向的头,也斑白了。
环视石渠流水环绕的大汉皇家图书馆,如山一般的学问知识时,刘向只在心中感慨:“扬雄或许没说错,这天下,确实不尽善尽美,并非太平世。”
但是,他如张骞一般,开拓了汉人的视野;像卫霍一样,扫清了帝国的敌人;效仿孔子,将海西贤人的“五经”也弄来了。又如同周公,以左传为契机,在贺国创造了一套开拓进取的礼仪制度,还逼迫得汉家天子也不得不效仿。
最后,他还像燧人、神农等上古先贤般,创造了诸多发明,使黎民受益。
这也是刘向如此推崇先师的缘故。
刘向将手捏成拳,仿佛握住了什么:“今世虽距太平尚远,但贺武成王,早就将致太平的钥匙,留给了后人!”
只是不知道,未来会如何,贺武成王为汉家开创的好时代,继任者们会怎样发展下去?
据刘向所知,贺国自武成王薨后,已经实质上分裂了,广袤的土地无法撑起一个像汉家一样的集权王朝。
任弘死前特地创造了“侯伯”这一职位,用来提高几位将军的地位——如今赵氏为北境侯伯,里海北岸直至黑海的广袤草原,由赵汉儿的后代统治。陈汤为南境侯伯,统辖南天竺和狮子国。王招军为西境守护,管着月氏诸部和安息东境的木鹿,这是任弘近十年来飞速提拔的小将。王凤为东境侯伯,与大汉安南都护接壤。
而新任的贺王任白,国土不过是河中、北天竺、西天竺、中天竺而已,被四大侯伯众星捧月,有共主之名。
贺国的权力疆域如何分割,刘向没法管也不太关心,他想知道的是,任弘死前心心念念,亲自命名的贺国大图书馆“天一阁”,修得怎么样了?
在任弘的计划里,希望汉家六经、诸子之学也能运去身毒,让贺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们能继续吸取母邦的文化乳血,莫要忘了自己的根。
而今日的石渠阁之会散了后,扬雄又来禀报了刘向一个好消息:“夫子……子,子俊回来了!”
子俊是刘向的小儿子,刘歆,年纪虽轻,却多才多艺,甚至胜过了刘向少年时,他十五岁就精通五经,能倒背左传,二十岁协助刘向编订《山海经》,在翻译海西诸子著作时也出力不少。
他三年前随刘向去探望任弘,之后便留在了那,负责贺国图书馆“天一阁”的构建,如今怎么说回就回了?
刘向让儿子立刻来见,也不顾他风尘仆仆,便训斥起来:“天一阁初立,百事待举,汉家书籍要印刷海运过去,海西大秦之书也要由天一阁翻译后送到石渠阁来。太后、陛下与老夫皆未召你,你岂能抛下公事匆匆归来?”
刘歆没料到许久不见的父亲是这番态度,只好道:“大人,非是小子怠慢天一阁之事,而是那边,已有了一位合适的柱下史。”
柱下吏就是图书管理员,老子曾做过的工作。
“哦?莫非是哪位西去的大儒?”
这些年,不单是活不下去的贫民、恶少年才西出阳关,前往贺国谋出路,部分真正有学识的人,也想去强盛的贺国谋个二千石——贺国不缺奴隶,最缺汉家知识分子。
刘歆却摇头笑道:“不是皓首老儒,那位新的柱下史,与儿年龄相仿。”
“与你同辈?”这下刘向有些惊讶了。
“是贺国东部侯伯王孝卿的侄儿,其弟王曼第三子,名秀,字文叔。”
王孝卿就是王凤,贺王后王政君的哥哥,如今算是国舅了,能力一般,但资历老,对任氏也忠心耿耿,王氏子弟年纪轻轻就混个郎官不足为奇。但天一阁柱下史这么重要的职位,非是博学之辈、学贯东西者不可担任,岂能儿戏?
但这王秀,刘向却是闻所未闻啊。
刘歆看出刘向脸上的担心,解释道:“父亲勿要担忧,王秀学识,虽在涉猎上不如小子宽泛,但钻研之深,却略胜过我。他常有惊人之言,还和武成王一样,作得一手好诗,曾与身毒大浮屠往来辩论,谈及佛性,作诗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使得那华氏城大浮屠反过来要拜他为师。”
“他尤其擅长格物之学,那海西欧氏的《几何原本》,很快便摸索精通,并能作新的解法与公式,贺国学界皆不如也……恕儿不敬,哪怕是武成王本人复生,在数术格物方面,恐怕也略逊于王秀。”
刘向越听越奇:“如此年轻的奇人,为何我未曾听闻?”
“此人出名太晚。”刘歆道:“他年轻时平平无奇,只是一普通王氏子弟。直到三年前,也就是武成王薨后,这王秀却像是被神点了智,变得聪慧起来,才有了种种奇行。”
“而后,王秀也同大人一样,改了名和字。”
刘歆如此说道:“他现在字‘巨君’,名为……”
“王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