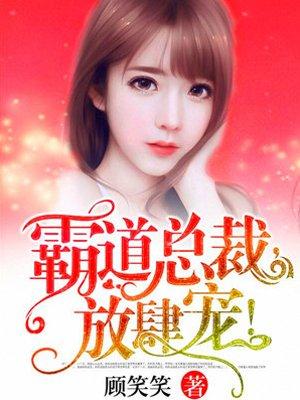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汉阙 笔趣阁 > 第577章 番外2 最后一个匈奴人(第2页)
第577章 番外2 最后一个匈奴人(第2页)
高原夜晚的酷寒,时常出没的野狼,以及忽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但真正的灾难,却是在他们跋山涉水,找到一支先零部落后开始的。
还没饮着热奶舒缓过来,这个小部落就遭到了袭击,石头和牦牛骨制作的箭簇射入营地,然后是嚎叫着冲杀进来的敌人,连醍醐阿达在内,所有没死的人都成了俘虏。
而第二天才看清,袭击他们的人,是与先零羌相似打扮,甚至语言都能互通的唐旄人。
醍醐阿达又成了奴隶,与唐旄人的游牧部落一起,辗转于这片后世被称为“羌塘”的苦寒土地。不是他不想逃,而是周围多是无人区,一个人几乎活不下来。
好在唐旄人是不断迁徙的,有时候他们会向南聚拢,一起发动战争,与他们的兄弟部落发羌进行殊死搏杀,只因为发羌占据的是温暖能种植谷子的河谷。
在唐旄待了三年后,醍醐阿达瞅准机会,再度出逃,这次他逃到了发羌。发羌大概是最早跨越高原的羌种,来得早,所以占据了一片沃土,种植高原唯一能生长的谷子。但和当初诸羌为了大小榆谷年年交战一样,发羌的周边也并不和平,他们经常和更南方,并不属于羌系部落的人进行战争。
醍醐阿达靠着一手好箭术在那儿站稳了脚跟,甚至拥有了妻子,生下了一些儿女——虽然大多数都夭折了。
他回家的心也慢慢淡了——主要是这么几年过去,醍醐阿达已经彻底迷失在了高原深处,虽也不忘经常向外出狩猎的人打听发羌周边都有哪些国家,但发羌几乎不与任何邦国接壤,面对一片空白的地图,醍醐阿达几次出走寻找无果后,只能又绕了回来,安心留下。
这一留,就是十多年。
在他已几乎被同化成一个发羌人,在他的儿子已经能独立狩猎野牦牛的那年,发羌却迎来了来自远方羊同国的人,这是发羌第一次与外界沟通。
而醍醐阿达那颗想要回家的心,再度萌动了。
“我是匈奴人,我要去寻找自己的族人。”
他如此告诉自己妻子,背着弓,毅然踏上了归途。
长子和次子随他同行,他们跟着羊同人走了大半年,抵达了发羌西方数千里羊同国(象雄)都城。
是与羌人截然不同的国度,历史悠久古老,城池修在光秃秃的山崖上,面容晒得黑红色的土著警惕地看着外来者。他们信奉名为“苯教”的信仰,将尸体搬到山上交给秃鹫啄食,这点和拜火教有些相似之处。
在羊同,醍醐阿达时隔十多年后,第一次探知到了外界的消息。但羊同人口中的那些国家,与他印象中匈奴西南的诸国是否一致,醍醐阿达无从判断。
巧的是,次子爱上了一个羊同姑娘,醍醐阿达让他留下来,自己则与长子继续向北进发,进入了难兜国,这个国度供奉着因派系斗争而出走的印度佛教“雪山部”。
因为语言不通,鸡同鸭讲,醍醐阿达只能从当地人的描述中隐约听明白,在难兜的西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十年前从北方来到了印度……
“一定是匈奴!”
“难道是右贤王?”
醍醐阿达记得,当年的右贤王,是极力主张西进的,甚至希望能将匈奴整体向西迁移,避开强大的汉朝,而在安息、身毒之间建立王庭,奴役诸国。
这让醍醐阿达激动莫名,但让人悲痛的事再度发生,他的长子因为疾病,死在了难兜国。
醍醐阿达没有按照羌人习俗将尸体烧了,而是亲自挖了坟冢将儿子以匈奴传统埋葬,将儿子的弓放在墓上,轻抚与他告别。
“我是匈奴人,身上流着祁连神的鲜血,你也一样。”
接下来,醍醐阿达只能孤身上路,在葱岭和昆仑南麓的山系里辗转游走,和二十年前初入高原一般跋山涉水。
终于,在翻越一座座高山后,醍醐阿达看到了高原的尽头,以及郁郁葱葱的森林和农田遍布的平原,但一道关隘却拦在他面前。
更让人绝望的是,那关隘上旗帜的字,他认识——醍醐阿达一共就认识两个汉字,巧了,都在!
一个是“漢”,一个是“任。”
醍醐阿达愣愣地跪倒在地,哑然失笑。
二十多年前,为了躲避这两个字,他选择跟羌人一起,向西进入高原,最终将自己下半生几乎都耗在发羌。
而今日,时隔二十余年,绕了不知几千里几万里,兜兜转转,却又见到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