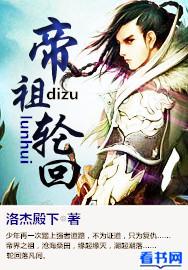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爱后即焚林啸也 > 15你还知道我会抽你(第1页)
15你还知道我会抽你(第1页)
他身上的药味那么重,刚一进来梁宵严就发现了。
发现了也没管,任由他鬼鬼祟祟地跟着,就想看看他要耍什么把戏。
结果他自以为毫无动静地弄出这么多动静,就为了送一条小船。
那天晚上梁宵严回家时,车上多了一把小花伞。
油纸做的粉色小伞,跟朵桃花那么大,撑开时也漂亮得像朵桃花,中间还有黄色的花蕊。
比记忆中的还好看。
游弋跟他前后脚回的家。
梁宵严车子进院,他翻墙进屋。
梁宵严下车看向楼上,他关灯拉窗帘,梁宵严抬腿往里走,他慌里慌张地脱鞋脱外套。
左脚踩着右脚把鞋踩下来,往床底下一踢,结果劲儿使大了直接给踢门口去了,着急过去捡又被裤腿绊住脚,“梆叽!”
一下大头朝下摔向地面。
“哎呀。”
腹部的伤正好砸上床沿。
“怎么了!”
小飞闻声从外进来,看到游弋生无可恋地趴在地上,好似一条扁扁的饼。
他一早就守在外面,小屁蛋子啥时候溜出去的他知道,啥时候回来的更是门清,全当没听见。
饼在地上挣扎翻面,没翻过来,抬手求他救命。
风呼呼吹动窗帘,枫树叶子哗啦作响。
咚咚,咚咚。
梁宵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小飞连忙将饼抄起来,卷叭卷叭塞进被窝,又冲向门口一左一右把两只鞋踢走。
刚踢完,门外“咔哒”
一声。
梁宵严握着门把手,下压,前推。
屋里漆黑一片,月光如沙般洒落,窗帘被风吹起来,窗外是灰蓝的天托着火红的枫叶。
他往床上看了一眼,打开灯。
游弋蒙在被子里呼呼大睡,露出来的头发上沾着片不知道从哪蹭来的草。
真是偷吃都抹不干净嘴。
“起来。”
他走到床边。
被子里的人没反应,但眼皮在飞速鼓动,一张小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急的还是烧的。
“去给他量下体温。”
“我不要!”
游弋一个猛子坐起来。
“你不是在睡觉吗?”
“听到哥……不是,听到你的脚步声就醒了。”
梁宵严懒得理他:“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