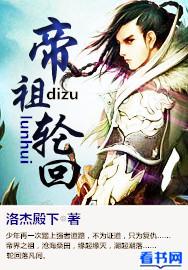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爱后即焚林啸也 > 34哥你怎么还不来(第1页)
34哥你怎么还不来(第1页)
他失声了……
他失声了……
他失声了……
这四个字如丧钟般在梁宵严脑中回荡,死去的是他身体中所有珍爱游弋的那部分血肉。
是他99%的血肉。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
梁宵严听到这句话的耳朵和那半边身体全部陷入麻痹。
疼痛如流水般浸透他的身体,干涸不了的不是潮湿的水痕,而是皮开肉绽的伤口。
人在痛苦到极点时,会开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刹那间,梁宵严失去了对外界的所有感知。
脑海中忽然插播了一段咿咿呀呀的旧色记忆。
那是他教游弋学说话的时候。
游弋说话晚,走路晚。
翻身、爬行、坐起来,学得都比一般小孩儿要慢。
他似乎在身体力行地证明着自己就是个拥有畸形脑瓜的傻孩子,别人都不要的傻孩子。
他五个月时才可以发出“啊、啊”
的声音,七个月时可以念一些模糊的单字,将近两岁时,都无法完整地说出超过三个字的短句。
梁宵严带他出去,有大人逗他让他叫人,他就只是咧开嘴巴朝人家笑,从来都不叫。
大人们并不会当着他的面说什么,就只是可怜地看着他,然后长叹一口气,就足以让游弋小小的心脏,感觉到理解不了又无法承受的疼痛。
他把小脸埋进哥哥怀里,两只小手圈着他,小小声地抽泣一会儿,然后吐出一个字:“笨。”
我是个笨蛋,给哥哥丢脸。
梁宵严揉揉他的脑袋,说不笨,当天晚上就买回来一本识字的图画书教他说话。
院里的枫树下,哥哥倚着树干,弟弟坐在他腿上,小豆丁和大豆丁面对面,一句一句地学话。
梁宵严:“啊喔额。”
游弋:“喔喔喔。”
梁宵严放慢语速:“啊——喔——额。”
游弋张开嘴,露出一口小豁牙:“啊——喔——喔。”
三个字,教了半个月都只能说对两个,还是漏风版本的。
梁宵严挫败地垂下头。
不是觉得弟弟笨,而是后悔自己教得晚。
小孩子哪有特意学说话的呢?
都是在和爸爸妈妈相处的过程中一字一句耳濡目染渐渐学会的。
可他们家没有爸妈,只有一个沉默寡言的哥哥,他有时候三天都不说一句话,要游弋去哪学呢?
游弋见状,也垂下脑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