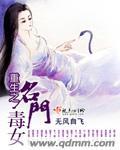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影视编辑器 > 第163章 一升再升(第2页)
第163章 一升再升(第2页)
苏宁起身走到窗前,望着院中那株在夜风中摇曳的海棠。
“兄长可还记得,”他突然问道,“那日徐阁老送我至二门,特意提起裕王府缺个纪善?”
张浩一愣:“你是说……”
“徐阁老既要我用,又要试我。”苏宁转身,烛光在他眼中跳动,“这《会计录》便是试金石。我若畏缩不前,便不堪大用;我若一味蛮干,便是不知进退。”
他端起已经微凉的茶,一饮而尽:“这个局,既要破,又不能破得太过。”
张浩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你的意思是……”
“账要查,但不能只查严党的账。”苏宁唇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陛下这些年修玄炼丹,内承运库的支出,是不是也该理一理?”
周正杰倒吸一口凉气:“你要碰宫里的账?”
“水既然已经浑了,”苏宁轻声道,“不如让它更浑些。”
窗外,初夏的夜风突然急了,吹得海棠枝叶簌簌作响,仿佛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
嘉靖四十二年的盛夏,北京城笼罩在一片溽热之中。
每日卯时三刻,苏宁便已出现在翰林院那扇朱红大门前。
晨光中的翰林院别有一番景致。
古柏上的露水尚未干透,几个老翰林正在院中慢慢踱步,手中捧着《贞观政要》或是《资治通鉴》。
见到苏宁,他们都会微微颔首,却不多言。
苏宁的书案设在翰林院东厢,紧挨着存放档案的架阁库。
这里原是存放前朝实录的地方,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陈年墨香和书卷特有的霉旧气味。
“苏修撰今日来得早。”
管理架阁库的老吏姓陈,已经在翰林院当了四十年的差。
他颤巍巍地打开沉重的铜锁,将一叠黄册搬到苏宁面前。
“这是嘉靖三十年的盐课总册,苏修撰要的。”
“有劳陈老了。”苏宁接过册子,轻轻拂去封面的灰尘。
陈老吏却不急着离开,佝偻着身子低声道:“这册子……三年前王御史也借阅过。”
苏宁抬眼看着老吏浑浊的双眼,会意地点点头:“晚辈明白。”
翻开厚重的册页,密密麻麻的数字扑面而来。
两淮盐场、长芦盐场、山东盐场……
每一处的课税数额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但细看之下,就能发现其中的蹊跷:同样是年产万引的大盐场,课税数额却相差悬殊。
“苏兄在看盐课册?”
一个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
苏宁不动声色地合上册页,起身拱手:“李检讨。”
来人是比他早三科的庶吉士李维正,如今已是翰林院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