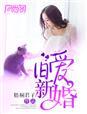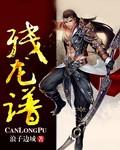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影视编辑器 > 第172章 隆庆认证(第1页)
第172章 隆庆认证(第1页)
时值隆庆二年的夏税入库期,北京城笼罩在闷热的暑气中。
户部衙门内,算盘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墨香与铜锈混合的独特气味。
尚书刘体乾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黄册与鱼鳞册间,眉头紧锁。
连年用兵、藩王禄米、百官俸银,样样都像无底洞,让这位掌管天下钱粮的大司徒时常感到捉襟见肘。
“大人!大人!”一名浙江清吏司的主事几乎是跌撞着冲了进来,手中捧着一份刚到的南直隶夏税汇总册,声音因激动而尖锐,“奇事!天大的奇事!应天府的商税……暴涨!”
刘体乾眉头一皱,接过账册,呵斥道:“慌什么!成何体统!商税能涨多少?莫非是哪家盐商又……”
他的话语戛然而止,目光死死锁在账册上“应天府”那一栏的数字上。
那是一个远超往年同期,甚至超过某些年份全年总数的惊人数字!
“这……这是多少?”刘体乾的声音有些发颤,指着那个数字问。
“回大人,是四十五万八千两!仅夏税一季!”主事激动地脸都红了,“去岁全年,应天府商税也不过三十万两出头!下官已反复核验三遍,绝无差错!”
“四十五万两……一季?”刘体乾喃喃自语,猛地站起身,“快!将应天府近半年的税课司明细,尤其是市税、门摊税、交易抽分的票拟,全部调出来!立刻!”
“是!大人。”
……
次日清晨,乾清宫东暖阁。
尽管放置了冰盆,阁内依旧有些闷热。
隆庆帝朱载坖看着户部呈上的奏报,脸上也露出了与刘体乾初时一样的惊愕表情。
“刘爱卿,这应天府的商税……可是核算有误?”隆庆帝将奏折递给身旁的冯保,语气中满是难以置信。
“回陛下,”刘体乾躬身道,“臣初时亦觉有疑,但已命人彻夜核对所有票拟、凭证。税款来源清晰,皆是南京、苏州、松江、扬州等府县税课司如实解送,绝无虚假。且……据应天巡抚苏宁附上的条陈所言,此乃‘商贸流通活跃,市面繁荣所致’。”
“商贸活跃?”隆庆帝沉吟片刻,“朕记得去岁此时,江南还奏报说市面有些萧条,怎地苏宁一去,就变得如此‘活跃’了?”
这时,一旁的内阁次辅张居正缓缓开口:“陛下,臣听闻,苏抚台在江南大力扶持一家名为‘大明供销社’的商号。此商号经营模式奇特,货物齐全,价格低廉,引得百姓趋之若鹜,分店已开遍江南各府。或许……税银暴涨与此有关。”
“一家商号,能缴纳如此巨税?”隆庆帝更加疑惑。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本固立刻出列,他素来与徐阶一派不甚和睦,此刻语气带着质疑:“陛下,事出反常必有妖!一家商号在短短一年内席卷江南,缴纳赋税竟堪比一省盐课,这本身就不合常理。臣怀疑,其中是否有官商勾结、虚报税银以邀圣宠,或是用了什么非常手段,盘剥小民,方才聚敛如此财富?”
刘体乾也补充道:“王大人所言,亦是臣之所虑。据下面人探知,那‘大明供销社’的伙计行事规矩得不像常人,算账速度奇快且从无错漏,管理之严格,闻所未闻。其东家周正杰,乃是苏抚台的表亲……”
话未说尽,但意思已然明了……
这很可能是苏宁利用职权,为自家亲戚垄断市场大开方便之门,所谓的巨额税银,不过是左手倒右手的把戏,或是竭泽而渔的结果。
暖阁内一时寂静,只有冰盆里冰块融化的细微声响。
隆庆帝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案,目光深邃。
……
就在朝堂上为此事争论不休,隆庆帝也心生疑虑之时,一封来自应天巡抚苏宁的密折,由通政司加急呈递御前。
密折中,苏宁并未过多为自己辩解,而是以一种近乎“报账”的冷静笔触,详细阐述了“大明供销社”的运营模式及其对赋税增长的贡献:
“臣查,‘大明供销社’分店五十余家,日接待顾客数以万计,涓滴成河,交易总额巨大,依法纳税,基数自宏。”
“该商号所有交易,皆用臣仿‘清账司’之法制定之账册,条目清晰,数额准确,无隐匿、无逃漏,故税课司可足额征收。”
“该商号所需货品甚巨,带动周边农户、工匠、船运力夫生计,相关行当交易活跃,亦贡献不少税银。”
“其售卖之南洋米粮等,价廉物美,迫使奸商难以囤积居奇,市面物价平稳,百姓有余财购他物,间接扩大了整体商税税基。”
“臣之表亲周正杰,仅为代管经营。‘大明供销社’所得利润,除维持运营和货款及依法归东家所有部分外,臣绝未沾染分文。所有税银,皆按《大明会典》足额缴纳,户部可随时派员核查账目、盘库清点,若有半分不实,臣甘当欺君之罪!”
最后,苏宁写道:“臣在江南,非为私利,实欲探索一条‘民富则国税足’之新路。‘大明供销社’或可为一试点。若此法可行,推而广之,则我大明财用匮乏之困,或可缓解于万一。”
隆庆帝看完密折,久久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