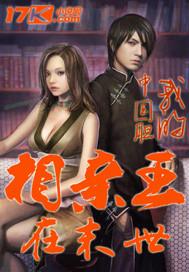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梦幻山海录 > 第93章 海舆秘录(第4页)
第93章 海舆秘录(第4页)
阿明皱眉:“星门?那是什么?经文中从未提及。”
“这就是问题所在。”徐衍叹息,“我怀疑海舆族自己也不完全了解星门,他们只是守护者,而非创造者。”
就在这时,一名学徒匆匆跑来:“先生,陈学士从京师送来急件!”
陈学士如今是翰林院掌院,负责整理古籍。信中写道,他在整理前朝密室时,发现了一批与海舆族同时期的文物,其中有一面青铜镜,背面刻着星图与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当地影吞日,天眼注视琅邪之时,星门将现。”
更令人不安的是,陈学士在信末补充:近日常有边陲村民报告看见“天空开裂”,有奇异光芒射出,随后又消失无踪。
徐衍面色凝重:“地影吞日是指日食。。。下一次日食就在三个月后。”
海舆司立即行动起来,分三路调查:徐衍亲自前往琅邪台;阿明去往那些报告“天空开裂”的村庄;陈学士则在京师研究那面青铜镜。
当徐衍重返琅邪台时,发现这座时隐时现的神秘岛屿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岩石上的古老刻纹比以往更加清晰,甚至出现了新的图案——描绘着星辰与一道开启的门户。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在岛上遇见了一位白发老妪,自称是海舆族最后的后裔。
“我族等待多时了。”老妪的声音如海风般沙哑,“星门不是灾难,而是考验。地海之眼不仅是平衡器,更是通道——连接着我们世界与其他世界的通道。”
徐震惊不已:“其他世界?”
老妪点头:“天地广阔,不止一方世界。海舆族世代守护的不是秘密,而是通道。每三纪,星门开启,两个世界最为接近。若人心平衡,则可互通有无;若人心失衡,则灾难降临。”
与此同时,阿明在边境村庄的调查也有了惊人发现。那些“天空开裂”的现象并非幻觉,而是短暂的维度重叠。他带回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物品——一块能自己发光的晶体,里面似乎封印着某种生命形态。
陈学士的研究则揭示了一个更大秘密:青铜镜上的星图指向的不是普通星辰,而是另一个世界的方位。他在古书中找到记载,称那个世界为“镜界”,与我们的世界互为镜像。
日食之日逐渐临近,世界各地异常现象频发:河流倒流,昼夜颠倒,甚至有人报告见到了“另一个自己”。
朝廷中出现了分歧:以宰相为首的一派要求封闭星门,认为异界接触太过危险;而以陈学士为首的一派则主张谨慎探索。
日食当天,所有人聚集在琅邪台。当月亮逐渐遮蔽太阳,天地陷入昏黄之时,惊人的景象出现了:海面上空,一道巨大的光门缓缓开启,门后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与我们的世界相似却又不同。
就在这时,一群黑衣人突然冲出,试图冲向光门。为首的竟是当年那位被说服的将军的儿子,他坚信门后有长生不老的秘密。
“不可!”徐衍大喊,“强行通过会破坏平衡!”
但为时已晚,将军之子已半身踏入光门。刹那间,光门剧烈波动,两个世界的景象开始重叠交错,风暴骤起。
老妪疾呼:“必须稳住通道!需要三心石!”
然而三心石早已融入地海之眼。危急时刻,徐衍恍然大悟:“三心石不是物品,而是人选!需要三个心意相通的人分别代表天地人三心,稳住通道三方!”
他立即指定:陈学士通晓天文,代表“天心”;阿明熟悉大地,代表“地心”;自己则代表“人心”。三人各站一方,集中意念。
令人惊讶的是,光门真的逐渐稳定下来。更神奇的是,从门中走出的不是怪物,而是一位与老妪相貌相似的老者——来自镜界的海舆族后裔。
“三纪轮回,我们终于再次相连。”镜界老者微笑,“上一次星门开启时,我们的祖先选择了分离,因为两个世界都未准备好。如今,或许时机已到。”
随着两个世界代表的会谈,真相大白:上古时期,两个世界本是一体,因一次灾难性实验而分裂。海舆族是那次事件后留下的守护者,等待两个世界修复创伤,重新连接。
徐衍感慨万千:“所以地海之眼的平衡不仅关乎我们的世界,也关乎两个世界的关系。”
镜界老者点头:“人心即地心,地心即天心,如今天心含两界。平衡不再是维持,而是融合与共生。”
此后,海舆司改组为“两界司”,负责两个世界的交流与平衡。徐衍担任首任司长,阿明和陈学士为副。
数年后,当第一个两界联合学院的学生在琅邪台上观星时,年轻的教师指着星空说:“记住,地理不仅是研究我们脚下的土地,还包括头顶的星空,以及星空背后的其他可能。真正的平衡不是静止,而是动态的和谐。”
远处,白发苍苍的徐衍微笑着点头。他知道,海舆族的使命已经完成,但人类探索与平衡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海风吹过,带来远处两个世界孩子们共同嬉戏的笑声。在那笑声中,似乎能听到古老海舆族的欣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