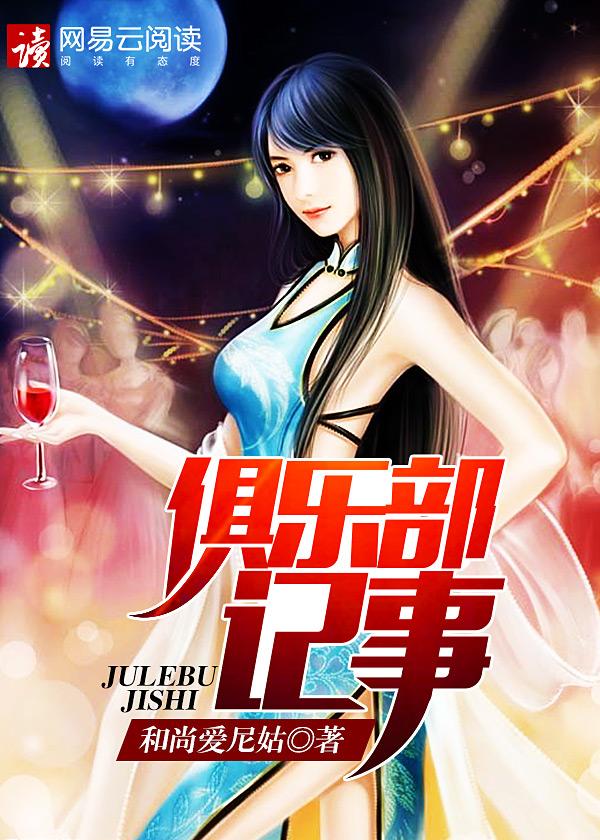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四旬老太守国门:对我精神不正常 > 第466章 盛放的人生十三(第1页)
第466章 盛放的人生十三(第1页)
李君欣没有立刻回答。
“……”
她走到窗边,望着楼下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高楼大厦间,偶尔还能看到几片等待拆迁的低矮老城区。
李君欣想起了自己童年时,街角那家总是飘着香气的糕团店,想起了外婆那双能绣出栩栩如生花鸟的手……。
那些记忆深处的温暖画面,与眼前冰冷的玻璃幕墙形成了鲜明对比。
李君欣转过身,目光扫过团队成员,声音平静却有力:“我明白大家的顾虑,从纯粹的商业回报来看,这个项目确实不划算。”
“但是,各位,我们‘君雅’的价值,难道仅仅体现在财务报表的净利润上吗?”
李君欣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些老手艺,这些即将消失的‘老街味道’,它们是一个城市的根,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密码。”
“它们可能不够‘潮’,不够‘快’,但它们承载的温情、匠心和对生活的热爱,是任何工业化产品都无法替代的。”
“我们有设计的能力,有传播的资源,如果我们都因为‘不赚钱’而选择视而不见,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它们一个个消失,最后只存在于博物馆的照片里吗?”
她的语气渐渐带上了一丝激昂:“而且,我相信,一个企业真正的成功和受人尊敬,不仅仅在于它赚了多少钱,更在于它为这个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留下了什么温度。”
“‘君雅’不能只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有时候,雪中送炭更能体现我们的格局和担当,这不仅仅是一个政府项目,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投入情怀和智慧的事业。”
她的话,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团队成员心中漾开了涟漪。
阿雅和小丁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触动。
“薇姐,你说得对。”
阿雅深吸一口气:“是我们目光短浅了,这个项目,我跟你!”
“也算我一个!”
小丁立刻举手:“不就是啃硬骨头嘛,我们又不是没啃过!”
……
“城市记忆活化”项目艰难启动,李君欣将其内部命名为“老街味道”传承计划。
她亲自挂帅,选择了项目中最具代表性,也被认为是最难啃的骨头。
位于老城区深处、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郑记”竹编铺,作为首个试点。
店主郑老伯年近八旬,脊背佝偻,双手布满厚茧和竹篾划出的旧伤痕,但眼神依然清亮锐利。
他的竹编手艺是家传的,据说祖上曾是为宫廷制器的匠人。
店铺又小又暗,挂满了各种筲箕、簸箕、竹篮,工艺精湛,却样式老旧,积着薄灰,生意惨淡,几乎全靠一些怀旧的老街坊偶尔光顾。
李君欣第一次带着阿雅和小丁上门时,郑老伯正戴着老花镜,就着门口的光线编一只小小的蝈蝈笼,手法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听到李君欣说明来意,是政府请来帮他的店铺做宣传、搞新设计的,老人头都没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政府?又是搞形式主义!前几年也来过一拨人,拍了些照片,写了篇文章,然后就没下文了。”
“我这手艺,老掉牙了,没人要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懂什么?别来耽误我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