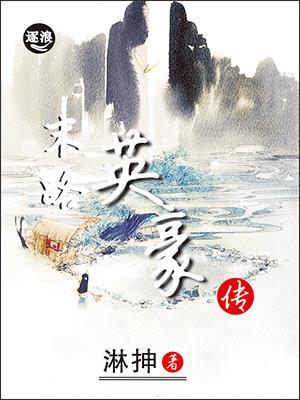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存活意义 > 第106章 日记4(第2页)
第106章 日记4(第2页)
赵星榆的眼神黯淡了一些;“我见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她说他们家本来就不富裕,现在女儿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医药费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白家派人去谈过,说愿意赔偿五十万,条件是让他们撤诉。”
“五十万?”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这些钱除去医疗费后,还能在现在的社会上干什么?”
赵星榆摇了摇头:“白家的人,从来都是这样视人命如草芥。所以我更不能让他们得逞。”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房间里再次被雨声填满。我看着赵星榆紧锁的眉头,知道她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如何应对这个案子了。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想我可以动用我的人脉。”我说道。
赵星榆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感激:“谢谢你。”
“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谢谢吗?”我笑着说,伸手揉了揉赵星榆的头发。
赵星榆笑了笑,然后正色道:“好了,我该回律所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我点了点头:“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赵星榆摇摇头,“外面雨太大了,你还是别出门了。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
我知道她的脾气,也不再坚持:“那你路上小心,到了给我打电话。”
“好。”
赵星榆拿起包,走到门口换鞋。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心里还是有些放不下。
“星榆。”我叫住赵星榆。
赵星榆回过头:“怎么了?”
“没什么。”我走上前,轻轻拥抱了赵星榆一下,“注意安全。”
“我会的。”赵星榆在我怀里蹭了蹭,然后转身离开了。
听着门关上的声音,我走到窗边,看着她的车消失在雨幕中。心里的担忧如同窗外的雨,越来越浓。
我知道,从赵星榆决定接下这个案子开始,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了。这场与白家的较量,注定不会轻松。
接下来的几天,赵星榆全身心地投入到案子的准备工作中。她几乎每天都泡在律所里,研究卷宗,会见当事人,搜集证据。而我再一次的和落雨见了一面。
锈铁门轴吱呀转,铆钉在掌心留微凉。水泥墙爬着黑铁管,铁丝网罩漏下的光,在铁架木桌上拼出网格。吧台后齿轮挂成墙,铜咖啡机正冒白汽,焦香漫过穿工装的客人袖口。有人用铁勺敲马克杯,当啷声撞在管道上。
雨丝斜斜地织着,将咖啡厅外的铁皮棚顶敲得噼啪作响。我拢了拢风衣下摆,盯着眼前女人指间燃着的烟卷。火光在她眼底明明灭灭,像溺在深潭里的星子。
“听说白家最近的事情吗?”我漫不经心的搅拌着咖啡,声音低沉,“就是白世青的肇事逃逸案。”
落雨手里的咖啡杯没动,侧脸贴着那扇蒙着层灰渍的窗玻璃。窗外雨势正猛,行人们抱着头在水洼里跌撞,她的目光像黏在玻璃上的雾,一动不动,倒像是对那些奔跑的身影着了迷。
“白世青……”我把银匙往杯底一磕,叮当一声,声音依旧沉得像浸了水,“不知道落雨小姐,对这位白家的纨绔子弟有什么看法?”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落雨还是没回头。指间的烟燃得只剩半截,灰烬在穿堂风里颤了颤,她连夹烟的手指都没动一下,自始至终,一口没吸。
“白世青的车胎痕迹,在城郊采石场被发现了。”沉默了许久后落雨吸了口烟突然开口,烟圈混着咖啡的热气扑在我脸上,“但有人用高压水枪冲了三天三夜,现在连法医都提取不到有效橡胶残留。”
我握着咖啡杯杯的手指骤然收紧,不锈钢壳传来冰凉的触感:“根据我的调查,交警支队的李伟昨天递交了辞呈,说是得了肝硬化要回老家养病。”我从怀里掏出个牛皮信封推过去,“他儿子在国外的学费,昨天被匿名账户结清了。”
落雨掀起眼皮,长而密的睫毛上沾着细小的水珠:“你觉得是白家做的?”
“除了他们还有谁。”我盯着落雨烟盒上印着的衔尾蛇图案,“肇事当晚,白世青的法拉利出现在监控死角的时间,正好与死者被撞的时间段吻合。”
烟蒂被摁灭在桌面上生锈的小铁桶里,发出滋啦的声响。落雨从帆布包里抽出几张照片,照片上的红色法拉利左前灯有细微裂痕,保险杠下方沾着暗红色的纤维—那是被撞女生衣服的材质。
“这些是我在法拉利送去检修前找人拍的。也怪他们运气不好,修车的老板我刚好认识。”落雨指尖点在裂痕处,“但检修厂老板今天早上‘意外’坠楼了。”
雨声突然变得狂暴,铁皮棚像是随时会被掀翻。我想起赵星榆昨晚红着的眼眶,她握着那份被篡改过的事故鉴定报告,指节泛白地说死者家属在医院被人威胁。原来那些不是空穴来风。
“白家正在清理痕迹。”我压低声音,喉结滚动着,“赵律师找到的那个小混混,今天早上发现煤气泄漏,现在还在ICU抢救。”
落雨突然笑了,笑声像碎玻璃刮过金属:“我想你急着见我,不是为了听案情。”
“那是当然。”我指尖在咖啡杯沿敲了敲,点了点头,“不过……倒是没想到,你会去碰这案子。”